童年與偶戲關係密切,不管布袋戲、傀儡戲或皮影戲都常接觸。在故鄉廟會看布袋戲時,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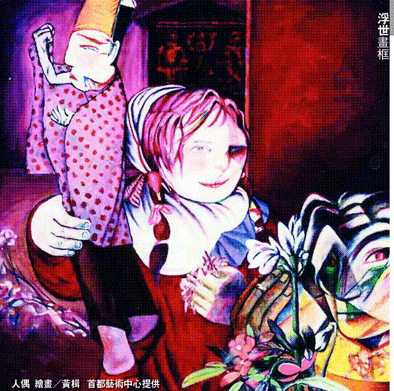 未開演就先搶占戲棚下等候;傀儡戲是開光或謝神的主戲,大人囑咐小孩要離遠些不可正視,但我常不聽話,總要偷窺才過癮,其中皮影戲與自己有其一段因緣,給予我更深刻的印象。
未開演就先搶占戲棚下等候;傀儡戲是開光或謝神的主戲,大人囑咐小孩要離遠些不可正視,但我常不聽話,總要偷窺才過癮,其中皮影戲與自己有其一段因緣,給予我更深刻的印象。
外婆家在有「皮戲窟」之稱的彌陀港的一個小漁村──海尾仔。小時候父母親常因生活困頓而起爭執,最後的結局就是母親拎著包袱帶著我回娘家,一住就會很長的一段時間,若逢烏魚汛期,漁民為了迎神守護烏魚能夠豐收,戲一班至少半個月,那時少有娛樂,演皮影戲把整個原本寂靜的小村落掀起一片熱潮。
海尾仔村不到十戶人家,有一半以上跟外公有親戚關係,外公有三弟一妹都在此繁衍後代。戲棚就搭在外公小弟我們稱「四公仔」的門腳埕一塊台地上,它面對漁塭與大海,視野空曠,景致宜人。
記憶裡那是冬至前後,朔風冷咻咻的吹著,在四公仔門埕前一棵枹仔樹旁,皮影戲正如火如荼地演著,人氣也愈聚愈旺,不覺寒冷,而我們小孩更是看得目瞪口呆,寸步不離,總要到戲散後才不捨離去,這時大都已夜深人靜了。
在海尾村大家把皮影戲簡稱「皮戲」,看皮戲都是全家總動員。晚餐後,夕陽餘暉中,大人小孩就搬著椅凳占位子,戲未演先轟動,戲棚下滿是人潮,今晚是文戲或武戲都已事先探聽好,男人(孩)都喜歡武戲,即神怪武打戲,如西遊記、封神榜、鄭三寶下西洋、李哪吒鬧東海、濟公傳等;至於文戲即較抒情,常以一段淒美的愛情或感人的親情去賺人眼淚,較受女性喜歡,如傻女婿拜年、蔡伯嘴、白蛇傳、五美再生緣、蘇雲過江等。
那是個還未有電燈的年代,戲偶是藉著油燈(點燈火仔)的光映照在小小的影窗呈現出來的,有時油燈閃爍不停,影像有些模糊;而戲台以牛車為主幹,顯得非常簡陋,但演者的唱腔口白以及握著竹籤操弄戲偶表演的功力,仍讓觀眾看得入迷。
當然後台的音樂配合演者的說詞才能使整齣戲顯得熱鬧、活絡、精采,而受到觀眾激賞、喝采把真情溶入戲裡;因此後台的動靜也常吸引著我,只見樂師六、七人擠在牛車上賣力的吹奏敲打。通常樂器有大小鼓、大小鑼、大小鈸、嗩吶、響板、橫笛、二胡、月琴、南弦子、四股弦子等,奏出高亢激越有節奏的戲曲,讓我聽得入神,烙下即使距今近一甲子的歲月仍印象深刻到難以忘懷。
童年最難忘的戲碼是孫悟空大戰牛魔王與蜘蛛精。尤其是孫悟空七十二變戲法,令人嘆為觀止。演者充分利用燈影玄幻的特點,再加上鼓樂聲交纏急奏助威下,孫悟空大喝一聲:「看我的七十二變啊!變啊!變啊!」手中的金箍棒平地飛起,在半空中霎時化成千百支棒影,活像千百條飛蛇凌空竄射,害得一群小妖精四處奔逃,看得我們小孩子拍手叫好,直覺過癮。
還有哪吒三太子腳踏風火輪,手持軟妖劍、砍妖刀、捉魔網、縛妖索、降魔杵等等十八般武器,勢如破竹,把妖魔打得落花流水,魄散魂飛,他威風凜凜的模樣,羨煞同是孩兒的我們,他是我們小時候的英雄。
時代在變,偶戲也風水輪流轉,在我國小高年級時,金光布袋戲興起替代皮影戲。幾乎迎神廟會都是布袋戲的天下,它聲光幻化多變,表演技巧創新,劇情曲折離奇,江湖味濃厚,對打撕殺一如真人表演,也因受觀眾歡迎而走進戲院,不像皮影戲只能黑暗中或夜晚才能顯現影像。這時偶爾也會隨母親回到海尾村,雖四公仔家門前依然有皮影戲公演,但觀眾大不如前,因鄰近的村落有演布袋戲而被吸引過去了。
五、六○年代電視來臨,多數人靠它充做休閒生活,舒適地躺在家裡的沙發上欣賞自己喜愛的節目,尤其黃俊雄演的布偶「雲州大儒俠──史艷文」電視劇,風靡很長一段時間,別說皮影戲,所有野台布袋戲、歌仔戲都無法抵擋而敗陣下來,這時每次到海尾仔探望外婆若逢皮影戲公演,我仍會前去回顧一番,雖然戲棚下只有小貓三兩隻,但操偶老師傅仍賣力演著,感覺只是在演給神明看,但也不難看出他們在為地方戲曲存留根脈。
皮影戲從台灣開拓時便伴著先民渡海來台,有它獨特的風味與特色,更蘊含著一份鄉土情懷,所以仍有許多人關切它的生存。
八○年代在今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岡山文化中心成立「皮影戲館」,收藏許多皮偶展示,也不定期邀請僅存的幾團公演,讓這種民俗技藝能延續、傳承下去。
二○○六年至今在鳳山衛武營的偶戲藝術節活動,皮影戲是重頭戲,我常捷足先登年年參與。看到新世代的孩子也湧入現場,凝視著、微笑著,看得入迷,偶爾也因劇情逗趣、精采而笑出聲來,常讓我懷念起童年看皮影的情景,一股溫馨自心底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