彎彎壺嘴似蛾眉 手做泥壺為阿誰
隨手捏成隨手碎 到頭還是一堆泥
這是十一世紀波斯(今伊朗)天文學家、數學家兼詩人奧瑪珈音(Omar khayyam 1050~1122),所著《魯拜集》(The Rubaiyat)中的一首四行詩,原波斯文由英國詩人費氏結樓(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於十九世紀後半翻為英文。二十世紀六年代初傳入台灣,由當時赴美留學生,後為麻省理工學院名教授、物理學家兼詩人的黃克孫先生,於一九五二年以流暢的中文衍譯為動人的七言絕句詩篇,黃氏學貫東西,天才橫溢,文采斐然、譯作刊行之後,立即掀起當時台灣文壇一股巨大的奧瑪珈音風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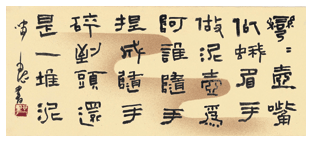 詩文一開始,鏡頭便扣住泥匠的巧手,將不起眼的泥巴和著水,塑成一只有著如女性眼眉般月彎形壺嘴的茶壺,教人愛不釋手。第二句則反問讀者,泥壺為誰而做?第三句歸入正題,論說「諸法無常」,泥壺隨時可以成,隨時可以壞,我們的生命不也如此?末句則道出事實真相,演說「諸法皆空」的宇宙真理,說宇宙萬法畢竟是空;說妙美的泥壺終究會歸於泥,歸於空的事實;說吾人的生命一如泥壺般終會歸於大地、歸於空的無奈。
詩文一開始,鏡頭便扣住泥匠的巧手,將不起眼的泥巴和著水,塑成一只有著如女性眼眉般月彎形壺嘴的茶壺,教人愛不釋手。第二句則反問讀者,泥壺為誰而做?第三句歸入正題,論說「諸法無常」,泥壺隨時可以成,隨時可以壞,我們的生命不也如此?末句則道出事實真相,演說「諸法皆空」的宇宙真理,說宇宙萬法畢竟是空;說妙美的泥壺終究會歸於泥,歸於空的事實;說吾人的生命一如泥壺般終會歸於大地、歸於空的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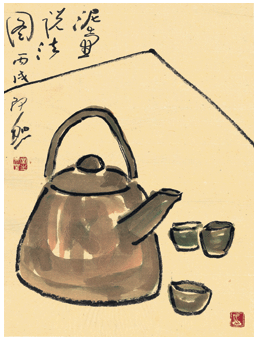 奧瑪全詩演說「成、住、壞、空」的宇宙真理,幾近佛陀說法,《金剛經》偈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宇宙萬物皆由地、水、火、風等「四大」所組成,並無不變的實體,泥壺是這樣,我們的身體也不會例外。原來西方科學最嚴密的思維極致與宇宙探索,和東方悲憫的佛法般若思想竟是相通的。
奧瑪全詩演說「成、住、壞、空」的宇宙真理,幾近佛陀說法,《金剛經》偈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宇宙萬物皆由地、水、火、風等「四大」所組成,並無不變的實體,泥壺是這樣,我們的身體也不會例外。原來西方科學最嚴密的思維極致與宇宙探索,和東方悲憫的佛法般若思想竟是相通的。
天台宗有謂「空」、「假」、「中」一心三觀;泥壺是由「四大」組合,以沒有自性,故是「空」,泥壺被稱為「泥壺」,只是人類給予之暫時假代的方便稱名,故是「假」,佛教並非否定泥壺的「空」與「假」,更非執愛占據泥壼的「有」;相反地,要藉壺之「有」,來超越壺之「空」與「假」,來修永恆不壞的慧命──沒有泥壺,我們不能泡茶喝水,沒有臭皮囊,我們將失去依靠,無從修行,無從成就慧命,假壺假身雖是「真空」,但仍有其「妙有」之用啊!
左上圖為「泥壺說法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