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靜肅莊嚴的金色蓮台上,祂贏得了永恆地崇拜與敬慕;是千年流傳不歇的神話與佛說塑造了祂,君臨天下般地面海昂坐,庸碌的凡人以熱切的顧盼,仰首向祂。千手觀音,的千手真能翻雲覆海,普度眾生嗎……
──〈千手觀音〉一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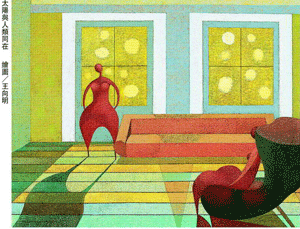
性別誤植
你和我及他,同樣地百思未解,詢之專研深諳佛理的上師似乎有著諸多詮釋;或說「佛」乃眾生,也就不必要索引世俗約定的性別之分吧?男身女顏,素衣或瓔珞何如辨識,男形就必得剛健,女姿就必得柔美,是這樣嗎?最初的賦予觀音人間型態究竟何者?筆墨的美學當以文字及圖繪呈露,那敬奉和傾慕一定不曾有絲毫地懷疑;那麼以慈悲定位的觀音菩薩,,真實的意象究竟如何確立才是?
你和我及他,一再苦思揣臆,是犯戒了。上師得知,是啞然失笑或祭以板罰輕懲,要凡俗如吾輩因之醍醐灌頂地猛悟六祖惠能偈語: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好了。此一智言歷代曉諭,比起〈心經〉、〈大悲咒〉還要熟稔、謹記。那為什麼你和我及他,時而還要窮根究柢的反問:觀音是男是女?似諳非懂亦不免思忖:佛世尊悉達多乃印度王子,何以佛教傳至中土,竟是肅顏慈目如漢人?藏傳佛教及中南美半島的諸佛之像似乎擬真於昔之天竺……這又是美學的相異了。
因之,千年觀音縱有千手千眼之慈悲大願,凡俗人間千年在佛以「無我」定義,時光流洄,大海潮浪依然,日月星仍舊,人的貪念、爭逐、戰亂、生死竟輪迴得那般微不足道。
但見上師拈花微笑,耐心的端眼環視座下惑者如你和我及他,反問:還在思索觀音大士是男是女麼?救苦救難當下,千朵蓮花,心香一瓣,淨瓶之水遍施雨露,甘美愁情,溫慰恩慈才是臻境;男身女顏,只是人間命題罷了。
觀‧自在
雖說「菩提本無樹」,回向佛理之人還是有緣。菩提一葉,上尖下圓,古代集其枯葉可以抄經亦能拓印佛圖;據說行走僧侶藏於袖間,荒野山村晚宿得以燃燭映照經圖誦之淨心。
這是我傾往的禮敬方式。心誠則靈,太多儀式性、群體性的形式不免流於催眠、約化的造作;猶若千年佛經可加以詮釋卻斷不可定於一尊。誠如蕭伯納所言:「寧可一人讀我之書有千般思索,而不須千人讀之僅有一種想法。」就像觀音千年,以木雕、石刻、筆墨行之,亦有不同法相,莊嚴有之、慈悲有之甚至嫵媚溫婉……千萬別囿於既定形態,心中有佛,自是如觀音臨群山,面大海,一切觀,自在。
寒秋身至日本京都名寺「三十三間堂」,敬拜千尊觀音全身立像;千佛如一,謁之儼然,但覺身心潔淨,如啜甘露瓶水。
初夏探訪中國敦煌「莫高窟」,飛天神女花舞繁麗,美不勝收,卻凝仰於觀音端坐蓮池,闃暗岩洞之間,清涼氣蘊若有芳香安頓。
彷彿一種母性的孺慕情懷。之所以疑惑於觀音原出於男女之辨,豈不因由佛、道合奉祭祀的「送子觀音」所引領的先入為主的直覺;是對是錯呢?但見尋常廟宇所列,觀音於中,金童玉女分侍兩側,瓔珞華麗於婀娜身姿,分明是神母慈顏,傾往、親炙也就成了必然。
千手千眼觀音則突顯雄性之剛毅,慈悲中含帶威嚴。是啊,已是「無我」的菩薩,不受生老病死所困,無盡的空間浩瀚,千年彷彿一瞬,法眼看見人間多端的觀音,縱然千手救苦,千眼憫難,又能真正救贖於貪婪人性多少?千手乏力,千眼盈淚,這紅塵苦難多不勝數,如何拯救,怎般教化,罪行在人,人未自知。
敬謁觀音三十三
迷暗指引尋光
縱化千手千眼千種身
浮世怎是人食人
默念南無觀世音
但見覷紅塵聆聽亂聲
渡河數里敢請問
千手千眼如何度凡身
以詩替之大哉問。這是我的朦昧或無知?詩的前段是夢中浮現的字母,明晰透澈地──
冷的火焰一朵蓮
水靜止思不淨
我是瓣葉下聽經
卻睡著的,魚
觀,自在。愚騃、散漫之我回溯甲子將至歲月,其實多的是不自在,少的是幸好有文學得以救贖;那麼何以時而會在不意中浮現觀音的慈顏善目?是童少時疏離的母愛或是已臨初老之年,還坐困未能修身、淨心的難以放下?
觀,自在。原來心不定,一切就不自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