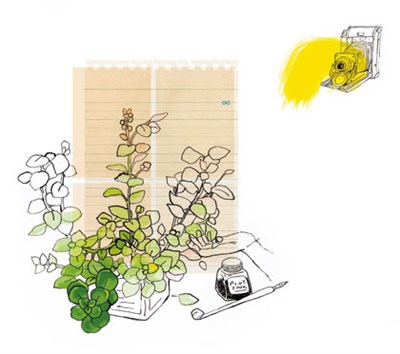 圖/林役勵
圖/林役勵
文/林文義
1
捷運文湖線在松山機場站由地底斜上,黑暗漸晰天光駛向高架地面層,右方車窗難得的近覽機場全景;但見航站停泊著一架架鯨豚般的客機,列車在這段軌道間必須緩慢速度,因為抵達下一站中山國中處有個半圓形大轉彎。哇!飛機耶。乘客們不由然輕呼,帶著小孩的大人驚喜的指向,大多數人還是低頭玩手機。
平視而看,一號高速公路上車行飛快,幾人辨識到高架路下是截彎取直後的基隆河?河對岸是我蟄居已十六年的大直社區,依山傍水的寧謐聚落;這是我尋常離家前往台北市中心的捷運行程,惜於在黑暗地底乍見天光的明亮時刻,面向車窗外的機場放眼那大片空曠。
轉過彎道,車速加快。坐在最後一節車廂的我,不經意舉目的本能反射,彷彿不捨的遙送遠去的機場風景,竟見後車窗出現巨大的客機尾翼,綠底白地球十字星的長榮客機,魚般胴體彩繪著可愛的凱蒂貓圖案……看了下手表,這午後時光這架法國製造的A330班機,應該是準時從松山飛往日本東京羽田的航程。
大多數人不會在意這異常美麗的突兀窗景,他們依然低頭玩手機,肉身與靈魂已然被一片小小的微晶片控制;科技很偉大,科技很危險,愛恨情仇、悲歡離合都在掌中的手機裡,自我抉擇也被動的被科技決定。稱之:「智慧型」手機,是增長智慧還是智慧被掠奪侵害?捷運車廂隔窗,兩旁的樓廈接壤,水泥、鋼架中有人在辦公室會議桌旁,拍桌怒罵、凝重或狂喜的聽著業績報告,針鋒相對;有人在家居裡閒散、日常的按著電視調頻器,接受喬治歐威爾預言小說般地被逐漸失真、流於吃喝玩樂的新聞蠱惑,毫無抵抗的接收吞嚥這一切向錢看,豪宅、超跑、名媛、政客……樓中人是否偶爾會臨窗外看?窗景外是眼下永遠車潮擁塞得喘不過氣來的大街小巷,也許有小小的驚豔──霾氣滿城的角隅竟有一片
綠公園或老公寓樓下的牆垣、巷角一蓬火紅的九重葛,甚至有人在狹窄的社區中庭種了幾株山櫻,春暖時節,緋紅著妝點顏色……
2
當然透過相機觀景窗的視覺,是有特定的選擇性。移動對焦主體、切割龐雜枝節……學生年代攝影課程,熄燈、合簾的教室裡在午後第一堂課頓時闇暗;只聽得鄰座同學濃重的鼻息聲起落,幻燈片打在白幕上,黑暗中一朵瓣葉分明的紅色山茶花特寫,粉黃的花蕊纖嫩得猶若嬰兒之臂,背景霧般朦朧。再續一幀黑白影像,眾者不由然輕呼:這哪是攝影?是山水畫嘛!畫面靜泊小舟,依傍一方兀岩,岩上嶙峋的蒼松糾纏……教授肅言:這就是合成攝影,在暗房中完成。
四十年前,學校教育我,這是經典。
另一位擅於攝影且在電視台任職的老師則意在言外的提到一個陌生的名字:羅勃卡帕(R o b e r tc a p a),二戰時候最傑出的攝影記者。換另一種角度,你們會看見更廣大的世界……老師語重心長的說。二十年後,我佇立在異鄉窗外飄著大雪的美術館裡,終於和這在越南戰爭觸雷傷逝的攝影家素面相見,透過展示於巨大牆面的黑白影像;冬雪很冷,心眼很熱。
被剃光一頭雲髮,巴黎戰後的德國軍官情人、西班牙內戰中彈剎那一刻的共和黨軍人、流亡、哭泣的中國難民……恍然大悟的遙想起二十年前兼課老師的那句話:換另一種角度,你們會看見更廣大的世界。他暗喻是放懷以自然、自在的雙眸凝視,而不只僅透過相機的觀景窗,凝影片面的、部分的焦點作為主體。
遺忘很多年的《人間》雜誌,彷彿意味著曾經存在過的出版歷程,更多的其實是對青春年少時小說家陳映真先生的敬慕,居於文學而非政治……我信仰前者但難以苟同後者,卻不曾因之意識形態的相異而失去屬於陳先生文字美學的景仰。二○一○年五月中旬與作家友群旅行中國大西北的敦煌,回程北京祈盼得以拜訪養病中的小說家,據說他斷然拒絕。無以面見誠屬遺憾,我卻念及他真摯著力過的《人間》雜誌,那些陰暗、深沉的文字與攝影,台灣社會底層的現實困境卻不向命運低頭、堅毅的生民靈魂。人道主義近乎宗教救贖的理想情懷盈滿這發行四年的刊物,如今依然未返的陳先生滯留北京,揣想他是否思念台灣原鄉、大嵙崁溪右岸的鶯歌小鎮童年?紫禁城壯麗的千年古都真的全然是熟稔的孺慕,或者還是陌生?彷彿是遙遠的窗景……回看自我在更早的年少歲月翻讀〈將軍族〉時的驚豔及悸動,引領我往後整個從禁制到逐漸解放的八○年代,毅然行踏台灣各處,試著深入了解人民與土地的訪察與描述,悲喜互熾的學習謙卑和虔誠。依然是我心目中不朽的小說家,依然是我時而惦念、牽掛的最美麗的文學靈魂……拂曉前仍未眠,靜靜擦拭著一整套已有塵漬的《人間》雜誌,看著一頁頁遙遠的影像,土地與人民恆在的台灣,充滿由衷的關愛,而昔時以雄心壯志創構的人,長居兩千公里之遙的中國北京,異鄉當有夢,但願一切安好如初。(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