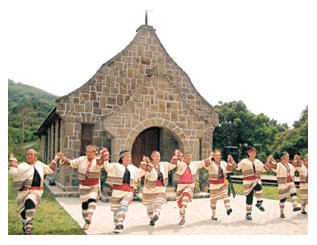
圖說:桃園縣基國派老教堂全部用石頭砌成,極具文化特色。
大龍峒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陳應宗表示,如果將閒置空間好好規劃、運用,是一件好事,但問題是主其事的執政當局哪來的文化?他質疑主管部門根本不知道文化為何物,哪來的文化?台灣的文化有待覺醒,有待提升。
陳應宗指出,文建會美其名要結合民間文史工作者,打造地方文化館,但是大家都是在打爛仗,因為文建會的經費都被地方民代、中央民代搶食一空,像他們這些默默耕耘的文史工作者,幾十年從來沒有拿過政府一毛錢。
陳應宗認為,政府的文化政策應該合理化,文化資源必須適當分配,而不是只是喊喊口號,什麼都不懂,政府應該對「正牌」的文史工作者提供適當的協助。
有人打著文史工作旗號騙政府錢
陳應宗說,有很多打著文史工作者旗號的人,根本就是在騙政府的經費,他們認為政府有「好康」可A,這些人的文化目標是搖擺不定的,純粹是為文化而文化,很容易就為政府單位所收編,因為,政府只要丟出一些肉骨頭或碎肉,他們就會爭相啃食,忘了自己的任務跟目標。
北台灣文化守護聯盟召集人林啟生指出,任何與文化有關的建設,多多少少都會有貢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不過,文化建設很難立竿見影,需要長時間才能看出效果。
他認為,文化建設要因地制宜,針對特定族群、特定社區、特殊文化而有不同的政策,因為每一個區域的文化版塊不一樣,例如台北市文山區和大龍峒文化一定不一樣,萬華和士林也不一樣,每一個地區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要了解各地文化特色,進而延續其內涵,否則空有硬體建設而沒有內涵,再美麗的建築,還是無法吸引人潮,文化館當然只有成為蚊子館。
林啟生強調,地方文化館的規劃要著重文化特質、地方脈絡及區域特色,最重要的是要符合當地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而且軟體、硬體建設同時並進、逐步建設。林啟生說,文化館重要的是主體性、是精神,只要文史工作者加入,地方文化館就有其生命力。最重要的是,地方文化館應該由地方文史工作者主導,才能符合當地的需要,成為真正的精神糧食。
船仔頭藝術村文教基金會董事謝敏政表示,一個國家當然需要國際級的博物館,但是也需要小型的文化館,藉以培養大家的文化素養,即使是「文化沙漠」也需要灌溉,一經灌溉,沙漠也會變綠洲。
謝敏政指出,催生一個地方文化館並不容易,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根本,政治人物用經濟效益或參觀人潮來衡量文化館,才會將文化館講成是「蚊子館」。謝敏政說,過去大家都嘲笑嘉義縣是文化沙漠,但是在嘉義縣政府的努力爭取下,全國文藝季陸續在東石、新港、梅山舉行,逐漸喚起當地居民重視文化、環保工作。
不應以經濟效益或參觀人潮衡量
謝敏政強調,文化館的存廢不能以「經濟效益」或是「參觀人潮」來評量,如果以參觀人潮來決定其存廢,那麼台北有龐大人潮,台北文化館利用度最高,為何故宮南院選擇在嘉義縣設置?
謝敏政說,難道像雲嘉南偏遠地區就不需要文化館嗎?他表示,雲嘉南地區居民過去受到的文化刺激較少,如果有地方文化館,就多了一個接受文化刺激的機會。
謝敏政強調,一個國家需要國際級的博物館,也要有小型的文化館,才能培養民眾的文化意識,文化沙漠只要灌溉也能成為綠洲,即使是「關蚊子」的蚊子館也可以變成文化活動的搖藍。
謝敏政說,以前嘉義縣也有所謂的「蚊子館」,三、四十年前,嘉義朴子的刺繡名聞遐邇,後來逐漸沒落,近年來,在相關人士努力奔走下,將一處閒置空間規劃為「朴子刺繡館」,結果由於成效卓著,連帶地刺激附近居民發起改善、美化街道運動,進而形成魅力商圈,養蚊子的地方竟成為朴子文化產業交流站,這是當初所始料未及的。
謝敏政表示,打造地方文化館不容易,大家應該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文化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如果閒置空間獲得充分利用,就能成為文化中心。他強調,每個地方、社區的文化特色不盡相同,就像社區總體營造一樣,文化工作要靠大家一起同心協力來做,而不是靠單獨一個人離群索居埋頭做。
謝敏政說,以前北迴歸線公園也是名副其實的蚊子館,僅做為清潔隊辦公室,現在重新打造成太陽館,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有燈光、有街景的「城市光廊」。吳鳳公園也是典型的蚊子館,阿里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接手後,吳鳳公園煥然一新,現在已成為遊客進入阿里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美麗窗口。
另外,像布袋的海運大樓閒置十餘年,不只是蚊子館,簡直就是廢墟,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管理處成立後,將海運大樓妝點成布袋遊客中心,這些都是蚊子館重生最好的例子。
謝敏政說,「地方文化館計畫」讓全台各地的閒置空間獲得再利用的機會,由此可見,只要大家用心、只要大家關心,就算是蚊子館也會成為「地方文化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