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各地方性格不同的城市正符合現代漫遊人特性:當你不喜歡一處城巿,只要搭上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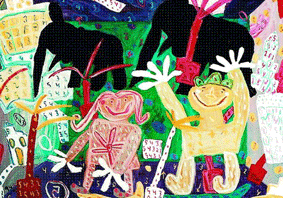 班開往東部或南部的列車,就可以隨時離開,前往另一處城巿重新開始。
班開往東部或南部的列車,就可以隨時離開,前往另一處城巿重新開始。
嚮往著城巿與城巿之間的游移,只因為人們經常需要改變。城巿與人一樣,很難固守某個小地方一生一世。離開,其實是為了保持距離感,因而選擇站在另一個遙遠的角度來愛它。
回顧過去,緬懷六○年代曾經風行一時的台語電影《台北發的早車》、《高雄發的尾班車》,娓娓訴說關乎台北的記憶是從一條黑色鐵軌開始。在夜裡,它無止盡地向北方延長,於昏暗燈光搖曳的車廂內入座後,眾人漸漸安靜了下來,於是他們忍耐地閉上雙眼,在睡夢中迎向台北。此時此刻,火車終於再也忍不住似地顫動了一下,從蒸汽口裡發出一口心不甘、情不願地深深長嘆,然後咕噥著趁星夜出發,直到黎明昇起。
見證七○年代序幕落下,繼一九七九年台灣西部幹線鐵路電氣化全線完工,蒸汽火車正式走入歷史,柴油火車與電氣火車相繼代之而起,只留下記憶裡曾經存在的聲音面貌。
聲音,除了見證列車行進運轉之外,還包括那些在冷空氣中飄蕩著一絲溫暖的車站叫賣及月台廣播。
早年火車停靠月台時,曾經多麼讓人印象深刻地總會出現流動小販推著餐車招呼:「便││當、便當、燒的便││當」,聲音宏亮卻非嘶喊,舉重若輕般頗具節奏感地沿著車廂外兜售。
另外也有在車廂上販賣物品的小販,揹著的木箱子裡裝載了飯盒和各種零食及書報雜誌,他們通常一車車地叫賣著:「便當、紅蛋、香菸、口香糖、鴨蛋、肉粽、報紙││」乘客少時,他們輕鬆地走,乘客擠得水洩不通時,他們也一樣走,只是速度慢了。
有趣的是,當遇到查票員過來時,那些眼尖的無照小販就會很急切地對身邊有座位的乘客說:「腳抬起來,快,腳抬起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乘客,都會莫名其妙地配合著將腳抬起來,這時小販就將他揹著的木箱子,塞到乘客的座位下,等到查票員走開了,小販又叫著:「腳抬起來,腳抬起來」。這時乘客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當然也很配合地抬起腳,讓小販將他吃飯的傢伙拉出來,繼續做生意。對此,車上的鐵路局人員其實都心知肚明,但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斷絕他人的生路。所以車廂內永遠都是熱熱鬧鬧的。
「第一月台即將進站的是九點四十分,開往某地的莒光號列車」,一旦火車進站,月台上總會傳來如此陣陣親切溫柔的播音語調,提醒旅客火車就快到了,可以準備上下車。
對於經常進出火車站的旅客來說,一聽見這聲音,大抵多少能夠令你暫時停下原先騷動急促的心思與腳步。在某種程度上,它甚至就像是代替熟悉親人向你我揮舞雙手問候告別的喋喋叨絮,也像是老家吟唱流傳許久的鄉音古調。而這類廣播內容除了一般常聽到的國語、台語或英文之外,據說早期台鐵在花東沿線大站(台東、知本、玉里及花蓮)甚至還曾請一位「台東之音」電台的原住民播音員預錄阿美族語的發車訊息,但隨著台鐵陸續更新自動播音系統,如今則是僅剩花蓮站內還有「真人版」原住民語播音。
無論是從保存歷史資產或促進觀光文化產業各方面來看,台鐵實在應該盡心設法找回這些早年正港「台鐵味」十足的最美的聲音。
晨昏時緩緩來往於鄉野,懷想起午後陽光灑進老舊的深藍色車廂,照在地板上宛如快速流轉的動畫,一個個可以打開的窗戶吹進的是自然風、耳朵聽的是火車疾駛吵雜的懷念聲、坐的是懷念的復古藍綠色膠皮座椅,這些其實不外乎都是古早時代我們對火車的印象。
從思念到鄉愁。
移動的鄉愁,搖搖晃晃地維繫於南北往返異鄉與家鄉的情感線上,你我在火車進站離站的輪迴節奏中,完成了漲潮退潮的生命形式。寄寓在遠方遊子內心深處,最遙遠的地方其實不是異鄉,而是自己的家園。
小小一座海島,南北差距三百公里,由彼至此卻有著迥然不同的空間面貌。北部城市慣見的陰濕多雨,隨著整列車廂緩緩朝向南台灣行駛,慢慢地,你會聽見雨停了,不久,窗外灑落一地的永恆陽光即開始驅散那份鬱鬱憂愁,轉眼間便來到了椰影婆娑的南方小鎮。火車的流動,透過總長五千公里以上遍布北部盆地、西部平原山岳、花東海岸和中南部地區的環島鐵路系統,讓人充分體驗了台灣季節與城市之間的奇妙遞換。
一條縱貫南北的鐵道貫穿了古早台北城,從市區幹道的肚腹間裡邊駛過,每隔一段時間總要搬演著柵欄升起「噹噹噹」警鈴迎向長串火車穿行市街輾在鐵軌上「框鐺框鐺」的聲音戲劇,此時交叉的車輛行人一律暫時停止,彷彿靜候著劇情結局揭曉前的那份屏氣凝神。
在一切市政建設皆朝向前方視野挺進的步調下,漸次消失於城市生活周遭的鐵道印象早已模糊,從筆直的中山北路到兩邊鋪著紅磚人行道的舊圓山橋(明治橋,後由國府更名為中山橋),人們從此不再聽聞火車行經馬路旁平交道柵門開闔之際,響起的噹噹聲音。
九○年代過後,經歷如此一段段看似長久卻總是乍然讓人措手不及的年歲裡,火車漸從地面遁入了地層下,橋上捷運的出現改變了台北天際線景觀。隨著二○○八年台北松山南港段鐵路工程全面地下化,昔日緊貼著城市街道視線所及的鐵道記憶,就此完全深埋地底。
時間,如何可以待價而沽?我們一出生就跳上奔向懸崖的火車,無論早晚,人終究要走,而懸崖則象徵死亡,是無法改變的宿命,但我們還是有所選擇,當火車遇站而停時,不管是選擇下車看看,或留在車上,火車都還是得繼續前行。
除此之外,當視覺景觀幾乎壟斷現代城市生活印象時,人們是否亦需另行尋找一種由聲音串起、穿越人造城鎮與自然地貌交界的空間記憶?
當前集結了時間、速度、效率於一體的台北捷運地鐵,在完全以數位監控的系統下僅屬冰冷單調、不留絲毫情面的科技流動,悉聽車輛進出月台鈴聲如是充滿了機械冷感所散發的疏離意味。相較之下,傳統鐵道火車本身極具視覺化的機械運轉節奏與汽笛白煙裊裊,車輪和鐵軌接觸的嘈雜摩擦,總是更能叫人乍聽百感交集、意蘊綿長。
音樂律動與火車運行的存在形式,皆可謂建立在揭露時間延展過程的共性特徵上。若從聲音物質角度窺看,在這當今已屬數位時代殘存的類比黑膠唱盤載體圍繞音軌溝痕隨著唱針徐徐畫過留下的,難道不也是尋求著如同蒸氣火車鐵道指涉視聽感官物理性的綿延眷戀嗎?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