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三仙台的三座仙山,並沒有醜陋的拱橋和世俗相連。雖然幾塊礁岩的面積不大,只不過是蒼海一粟,隔著淺水和陸地若即若離。從本島遙望也好;涉水登岸也好,海中礁岩總是帶著有仙則靈,神秘莫測的感覺,或許多多少少還保留一些稀有的、特有的動植物生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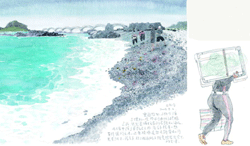
記得為了要不要有一座可以和礁岩溝通的橋,中央與地方曾經有「建設地方」或「維護自然景觀」之議,透過媒體隔著民眾頭上的一團迷霧互相指責。然而建或不建,只不過是兩位政治人物,在仕途上互相較勁的籌碼話題而已。
終於,主張繁榮和進步的一方略擅勝籌,一座既不好看;又不好走的「拱拱拱…橋」,於焉肇建。遊客們在休閒、觀光的驅策下,被一座奇怪的橋吸引著不遠千里而來。他們不知道在陸地外的熱帶礁岩裡有些什麼?
先通過停車場附近叫賣的攤販群,拗不過天性愛吃的本性,購足了一路上吃、喝的食物。再是談笑風生,用自以為消遙寫意的過橋方式,踏上一波又一波上下起伏的橋面,不辭辛勞終於到達了彼岸仙山。下了橋,只有一條安全小徑引導著簡單的環島一圈,除了聽到畫眉的歌聲和偶爾出沒在礁岩上的藍磯鶇之外什麼都沒有。不但沒有仙、沒有寶;沒有奇花異草;沒有珍禽異獸,更沒有任何遊樂設施,多數人都有受騙的感覺。吃的、喝的沒有了,垃圾就地丟棄,回程再要面對一座「拱拱拱…橋」時不免唉聲嘆氣:「來到這裡到底要觀什麼光呢?」上階梯;下階梯,一波、一波、又一波,更要咒罵幾句:「熱得要命 !大老遠跑來,什麼也沒有 !」心情喜怒隨著拱橋起伏,腳步也不像來時逐波踏浪那麼飄逸了。
人間這邊的海岸上,有兩個當地婦人從遠方沿著海灣,在數不清的細石堆裡尋尋覓覓。她們背著簡單的行囊背包,全身衣巾包裹,在大太陽下低著頭,一步一彎腰,仔細尋找有價值的寶石美玉。原來盛傳海岸山脈蘊藏寶礦並非空穴來風。在自然的營力中,進退不息的海浪下,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片斷被沖刷上岸。只見尋寶婦人先撿拾在手中初步篩選,然後收納在背袋裡,每一折腰都有收穫。
尋寶果真那麼容易嗎?我們搶在婦人前頭,彎腰、跪地、埋首……,用盡了貪婪的眼力和嗔痴的野心,也只找到了外表晶瑩的石英和玻璃碎片。或許曾經掌握了一些有價值的璞石,但是因為不具慧眼又從手中縱放了去。兩婦人已經習慣了輕佻的觀光客,經過我們眼前也不搭理,繼續以她們尋寶的步伐前進。望著躅踽的背影消失在拱形橋下,讓我想起米勒畫作中「拾穗」人物的身影。
台灣東海岸「尋寶」的婦女,用辛勞、汗水,來來回回灑在炙熱綿長的海岸線上,在海水與陸地的夾縫中;在保護與破壞的矛盾中,從遊客腳下踐踏的石頭堆裡尋找珠璣碎玉。
她們手上拿捏的不是美粧用的金珠,也不是可以豪華氣質的寶玉,只是生活的細節;背上沈甸的不是萬貫身價,也不足以用來榮耀虛偽,而只是家計和負擔而已。我常常以為寶物的價值是否和這些勞力、辛酸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