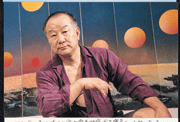 五十年代末期台灣的美術界在與大陸、日本隔離情況之下,美國現代主義風潮趁隙傳入,掀起了一陣現代主義的狂熱。劉國松在此階段的台灣美術史上是關鍵性的代表人物,創立以現代繪畫為主的「五月畫會」,在台灣致力提倡現代畫之抽象取向,引發了現代畫論戰,對於中國水墨的現代化理論推展及美術創作上有一定的影響。
五十年代末期台灣的美術界在與大陸、日本隔離情況之下,美國現代主義風潮趁隙傳入,掀起了一陣現代主義的狂熱。劉國松在此階段的台灣美術史上是關鍵性的代表人物,創立以現代繪畫為主的「五月畫會」,在台灣致力提倡現代畫之抽象取向,引發了現代畫論戰,對於中國水墨的現代化理論推展及美術創作上有一定的影響。
劉國松在美術圈裡是家喻戶曉的人物,甫獲國家文藝獎的他,終其一生都在為水墨畫的現代化而奮鬥不懈,不屈不撓地進行著他科學實驗式的藝術創作,大刀闊斧,勇往直前,為傳統國畫注入新生命,成為現代水墨運動最重要的推手,也被譽為「水墨現代化之父」,其精神與成就都教人感佩。
投下畫壇震撼彈
劉國松不僅在世界各地舉辦過上百次的展覽,當選台灣「十大傑出青年」,更獲得多項國際性邀展和殊榮,全球已有50餘家美術館和博物館收藏其作品,並被列入「美國名人大辭典」、「世界名人錄」、「成就人士錄」、「國際著名知識分子大辭典」,今年又獲得「國家文藝獎」。
提到劉國松,總讓人立刻聯想到台灣畫壇50年代末期的一個重要的繪畫團體──五月畫會,「五月畫會」的成員皆為對台灣的藝術發展深具反省與開創性的年輕藝術家,而劉國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劉國松針對水墨畫喊出「革筆的命」、「革中鋒的命」的口號,以及「先求異、再求好」的藝術教學方針,更是當時墨守成規的藝術環境所不敢思、不敢想的壯舉,為沉寂已久的台灣畫壇投下威力強大的震撼彈,其影響的漣漪泛及香港、中國大陸、海內外,乃至多年後的今日仍然餘波蕩漾,此不僅成為水墨畫領域必定嚴肅討論的話題,如今對此話題的熱烈反應甚至比起當年猶過之而無不及。
劉國松針對水墨畫喊出「革筆的命」、「革中鋒的命」的口號,以及「先求異、再求好」的藝術教學方針,更是當時墨守成規的藝術環境所不敢思、不敢想的壯舉,為沉寂已久的台灣畫壇投下威力強大的震撼彈,其影響的漣漪泛及香港、中國大陸、海內外,乃至多年後的今日仍然餘波蕩漾,此不僅成為水墨畫領域必定嚴肅討論的話題,如今對此話題的熱烈反應甚至比起當年猶過之而無不及。
原籍山東青州的劉國松,生於1932年,那是一個烽火戰爭的年代。劉國松隻身一人隨著國軍遺族學校來到台灣,進入師範大學藝術系,正式踏上學院的美術學習之路。在學期間重要的老師有水墨的傅心畬、黃君璧、溥儒、林玉山,水彩的馬白水,奠定了劉國松日後水墨發展的厚實基礎。
一下子得罪光台灣畫壇
除了水墨之外,劉國松也對西洋畫開始產生興趣,在朱德群和廖繼春老師的帶領下,開始對西洋繪畫進行研究,並對各種媒材技法作多方嘗試,如印象派的點描法和塞尚的結構分析等。在東西兩大繪畫系統的滋養下,劉國松展露了企圖融合中西技法的豪情。
到了1961年,原本以抽象西畫表現為主的劉國松,有感於一味追隨模仿西洋現代藝術思潮與畫風之不當,更對我民族文化傳統的發展與宣揚產生了強烈的責任心與使命感,故而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回歸本土,重拾東方畫系的水墨媒材,從事水墨的革新,倡導中國畫的現代化。詩人余光中當時還撰文稱劉國松為「浪子回頭」,讚揚他兼顧縱的民族性與橫的時代感。
劉國松不甘於模仿西方,但也不甘於抄襲古人,他想要走出自己的創作之路。他說:「我們既不是生長在古代的中國,也不是生長在現代的西方。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舊的;抄襲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襲中國的。」也就是說,我們既不該抄襲中國古畫,也不該一味模仿西洋油畫。如此一來,年輕氣盛的劉國松一下子將台灣畫壇的保守派和西化派都得罪了。這固然很快的讓他在畫壇闖出名號,但也樹敵無數。
有創意才能成畫家
劉國松追求中國現代畫的漫長路途,艱苦又曲折。為了開拓畫家的胸襟與視野,他吸收了西方的抽象精神,並且告別了中國繪畫中鋒的線和皴法的點,卻保留了水墨和棉紙的工具。他給予傳統文人畫所標榜的「筆墨」以嶄新的詮釋:「筆就是點和線;墨就是色和面;皴就是肌理。」同時更提出「革中鋒的命」、「革筆的命」與「建立二十世紀中國繪畫的新傳統」的口號,當時引起文化界軒然大波。
時至今日,他的理論已廣為海內外水墨畫家甚至史論家所接受,並形成一股潮流。在過去數十年當中,劉國松始終一面創作,一面教學,自己不斷地實驗與發明了許多新的技法,也創造出多種不同形式的個人獨特畫風。因為他一直認為,畫家與科學家沒什麼兩樣,畫家也要像科學家一樣,在畫室裡不停地實驗創造。他也以這種觀念從事美術教學,因此培養出一批不少的藝術人才,有的已在世界上嶄露頭角。
「我常對我的學生說,做為一個畫家與做為一個科學家沒有兩樣,科學家一定要全心投入在實驗室不停做實驗,實驗成功了才有所發明,有所發明才能成為科學家。畫家也 是一樣,他必須全心全意在畫室中不停實驗,實驗成功了才有所創造,有所創造才能成為畫家。如果一個人只知跟著古人的筆走,或老師教他怎麼畫他就怎麼畫,那又何異於科學家的助手呢?他自己是沒有什麼發明或創造的思想和理念的。」劉國松說。
大大擴展了中國畫領域
為了走出自己「中西合璧」的路,劉國松在西洋油畫的畫布上塗上石膏底,再用油畫顏料,做出如同水墨畫的崇山峻嶺、參天古木、雨雪紛飛的效果,達到一種物我兩忘的境界。至此,他已經初步創作出中西並兼,融合為一的作品。
29歲時,劉國松聽到建築師王大閎的理論,猶如當頭棒喝,使他放棄了中西合璧的石膏畫。王大閎認為,每一種建築材料都有它的特性,設計者應發揮原本材料的特性,而不是用另一種材料去偽裝,像是用水泥做出仿古的木造建築,然後塗上紅色油漆,就是做假。劉國松認為,用西方的油畫材料做出中國的審美趣味,這也是一種做假,於是他拋棄了已經發展成熟的石膏畫,回歸東方畫系的水墨媒材。
經過長期的研究和試驗,劉國松試用了幾百種不同的紙張,都不滿意,最後他發明了一種紙筋很粗的紙,並命名為「劉國松紙」,加上他以狂草入畫的筆法,創造出了獨特的「抽筋剝皮皴」技法。他運用紙張本身的紋理,在紙上撕下粗糙的紙筋,因此在畫中就顯出絲絲宛如電光火花的紋路,在巉岩中穿越併發。這些作品不只看來栩栩如生,而且肌理優美動人。
什麼叫「皴」呢?劉國松說,每到嚴冬時,人們的臉和手腳就被凍得龜裂,這種現象就叫作「皴」,用現代的名詞來說,就是「肌理」。肌理並非一定要用筆才能畫出效果,它可以用任何工具做得到,就如同他用撕紙筋的方式表現一樣。而劉國松這樣的概念,大大擴展了中國畫的表現能力與領域。
最敏感的現代畫家
由最早的「抽筋剝皮皴」所發展出的抽象山水,到遊覽歐洲瑞士雪山所畫的「雪山系列」,劉國松不斷的嘗試新技法,創造新的系列。之後就是「太空系列」,那是劉國松由美國阿波羅號登陸月球得到靈感,劉國松也在太空畫中,首次採用噴霧法,把水性顏料噴在畫面上,形成漸層或淡化效果。太空畫很容易明白,加上色彩非常鮮明,畫面構圖突出,是劉國松最出名的作品。在紐約展出時,被譽為「最敏感的現代畫家」。
在香港任教期間,劉國松研究「水拓」技法,利用顏料與墨在水面上自然流動所形成的波紋為基礎,在其上作畫。水拓的形象千變萬化,為畫家的繼續加工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基礎。至此,劉國松以傳統山水畫的基因培養現代水墨畫的種子,從而造就出一個千奇百怪、不沾人間煙塵的神秘世界。
劉國松在2000年前往珠穆朗瑪峰,觀看西藏雪山的奇景,出藏之後左耳突然失聰,多方治療都不見效果。劉國松記得:「我們到了6千多公尺,也就是到了珠穆朗瑪峰上面的探險基地,那一片壯麗的景象真是讓人心胸都為之開闊起來。回程的時候一到成都,下飛機時,忽然之間,我的左邊耳朵就聽不見了。」
劉國松說:「上天對我也不薄,還為我留下了一隻耳朵,以後我聽好聽的話就用右耳聽,不好聽的話就用左耳聽。」
這次的西藏之行,讓劉國松變成重聽,不過也因此發展出他著名的「西藏組曲」系列作品。劉國松回歸到一種具象美學的山水重探,他使用麻筋為主的「劉國松紙」為材料,以綿延的大山為表現主題,構圖幾乎全以宏觀鳥瞰的方式來寫景造境,充分傳達了他對西藏山區雄渾景觀的體會,以及對天地氣勢的感動。透過他的紙、筆、墨、彩,讓山、石、雲、雪、霧等自然元素,以不同的層次交織出一幅比傳統山水畫更具立體氛圍的傑作。
去年的成都雙年展中,劉國松的「西藏組曲」參展作品,其中一幅才剛掛上,馬上被加拿大收藏家預訂,成交金額新台幣400萬元。現身展場,沒有人不認識劉國松,他在世界舉行個展超過80次,全球收藏的美術館博物館近50間。
要畫到95歲
劉國松把現代水墨當成第一生命,問他要畫到幾歲?答案是95歲,自許為水墨傳教士的他,信仰就是現代水墨畫。
之後,劉國松又以「漬墨法」發展出色彩豐富多變的「九寨溝系列」,也受到藝術界與收藏界的高度肯定。
「九寨溝系列」使用不吸水的描圖紙為繪畫底材,劉國松放棄了大筆的書寫、馳騁的揮灑,以及材料拼貼的技法,而以細心的態度,利用紙的抗水性與皺摺、氣泡,以及墨和水在紙上的交流碰撞,創造了色彩斑爛的效果。劉國松成功地在「西藏組曲」崇山峻嶺的既有路線之外,又開發出一條微觀近物的山水新路線。
對於許多藝術家來說,一輩子能夠發展出獨創的技法或是畫風就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劉國松的繪畫生涯中,成功的研究出許多不同的技法,發展出許多畫風完全不同的系列,而且都發展的非常成熟,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劉國松以完全不同於傳統水墨的技法來作畫,在表現的形式上非常具有現代感,但傳達出的哲學思想和審美趣味卻是東方的,這更是令人佩服的地方。
自1961年劉國松提出「中國畫的現代化」,同時倡導「建立一個東方畫系的水墨新傳統」,迄今已快60年,影響了東亞儒家文化共同體其他成員國的水墨畫的變遷與發展,為此,去年4月北京經典文化的殿堂──故宮博物院,特別邀請劉國松在武英殿舉辦大型的《宇宙心印──劉國松繪畫一甲子》特展,以肯定其在中國繪畫的革新與發揚上的貢獻與成就,現在又獲得國家文藝獎,劉國松笑著說:「今生求仁得仁,我已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