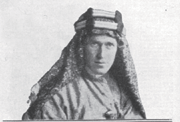 離開被勞倫斯稱為「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堡」酖酖克拉克騎士堡(Crac Des Chevaliers)回大馬士革的路上,凝望著窗外荒涼的黃土高原,腦海裡仍不斷浮現這位一代沙漠梟雄的傳奇事蹟。
離開被勞倫斯稱為「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堡」酖酖克拉克騎士堡(Crac Des Chevaliers)回大馬士革的路上,凝望著窗外荒涼的黃土高原,腦海裡仍不斷浮現這位一代沙漠梟雄的傳奇事蹟。
大戰期間經過媒體大肆喧染、報導,這位縱橫沙漠的英國軍官「阿拉伯的勞倫斯」一夜成名,戰後講演邀約不斷,然而就在名望如日中天時,他選擇隱姓埋名,投入英國空軍當個默默無名的小兵。蕭伯納(Bernard Shaw)、約漢本揚(John Bunyan)、哈代(Thomas Hardy) 與邱吉爾等文豪學者莫不對他讚譽有加。
誰料到天妒英才,他因車禍去世時才不過四十六歲。 勞氏屍骨未寒,有關他斷袖之癖,以及被虐待狂等揭私的負面論述陸續出籠。即便如此,卻動搖不了心中對「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敬仰。即便原本以為阿拉伯人會感激他的恩德,沒想到接受訪問的對象,竟然也語多保留,這點倒是始料未及的。
思索著自己是否掉入偶像崇拜的框架,全盤擁抱一個被神化了的凡人,完全漠視外界爭議性的批評,甚至把不中聽的責難視為陰謀論,必大加韃伐才甘願鳴金收兵。果如是,自己不就成了阿Q?
但反過來一想,二十幾年來心目中至尊無上的偶像,絕對經得起西方學者的考證與鞭笞。如果僅因為幾個阿拉伯人不經意的評論就信心動搖,那也未免太膚淺了。勞倫斯‧詹姆士(Lawrence James)在他的著作《黃金戰士酖酖阿拉伯勞倫斯一生的傳奇》(The Golden Warri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Lawrence of Arabia) 中的詮釋恰恰擊中心坎:
分辨兩個勞倫斯不難,一個是歷史人物,另一個是神話產物。這不只因為自己就是神話的創造者,他而且渴望日後的聲名能在歷史上留下印跡,成為『一名藝術家』。勞倫斯是成功地把自己一生演化成一件藝術品。
想起石棺上T‧E‧勞倫斯雕像旁邊,刻有他參加阿拉伯戰役隨身攜帶的三本書: 《牛津大學版英詩選集》、《亞塞王傳奇》,與《希臘神話》,腳下還有他考古收集的一小件雕塑,仍然覺得他像個舊識酖酖那麼熟悉、那麼親切。
一切人世間的得失毀譽,煙塵一般都已過去,卻仍改變不了勞倫斯在許多人心中的地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