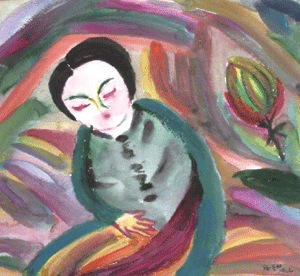 在森林中的木屋,身邊所傳來的是蟲鳴鳥聲和雨林中特有的香氣,那是林木和不知名花朵香味,尤其是在更幽靜的夜裡,即便是世俗世界的庸人在如此的環境下也會充滿詩情的。
在森林中的木屋,身邊所傳來的是蟲鳴鳥聲和雨林中特有的香氣,那是林木和不知名花朵香味,尤其是在更幽靜的夜裡,即便是世俗世界的庸人在如此的環境下也會充滿詩情的。
在網路e-mail的時代,突然接到一封用鋼筆書寫的來信,那一剎那,有一種回到遠古的感覺,許久未曾聞到的紙香撲鼻而來,原來是信紙上夾送的一株已經乾枯的野生蘭花,想不到,已然死去的花還殘留如此清新的香味,來信的人是已經十幾年未見的朋友,看看信封,這封信是來自沙勞越,婆羅洲的雨林,而郵票的內容就是一株野生蘭,寫信的人是楊,一位幾乎從我的記憶中淡出的海外友人。
楊是一位曾經在台灣留學的馬來西亞華裔學生,他的家庭是來自福建的移民,傳到他已經五代,世居於沙勞越的古晉市,一個有貓城之稱的城市,古晉在馬來西亞語中的意思就是貓,楊在信中告訴我;他終於成為國家所聘任的雨林保育員,而這個工作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標,現在,一周中有四天在雨林中居住,巡守,因為夜裡想起遠方的朋友,所以才寫下這封信。
看到那株野生蘭花,我想起曾經拜訪過的婆羅洲雨林,我可以想像他目前的心境是充滿寧靜愉悅的,在森林中的木屋,身邊所傳來的是蟲鳴鳥聲和雨林中特有的香氣,那是林木和不知名花朵香味,尤其是在更幽靜的夜裡,即便是世俗世界的庸人在如此的環境下也會充滿詩情的,所以寫下此信的心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他在信中說;婆羅洲的雨林面積有一半屬於印尼的管區,所以印尼方面燒林和盜林的事件頻傳,一個雨林卻是兩個世界,有時候,被焚燒的黑煙在馬來西亞仍清楚可見,而馬國政府也不止一次向印尼抗議,這兩個世界因為人民經濟差距很大,一邊已經知道保護森林,而另一邊卻仍忙著盜賣森林資產。
其實這樣的矛盾在這個世界已經不是新聞了,我們稱為惡意的掠奪,在以此為生的窮苦印尼山上人只能說是活著的所要條件而已。
我可以理解楊的無奈,就像十幾年前在台灣時他所遭遇的另一種無奈。
十幾年前,楊在台灣的工專留學時,認識了也是華裔的泰國僑生鄭,卻未想到鄭是來自泰北的孤軍第二代,當年一架飛機把她們從泰北送到台灣,應該是蔣經國的末代統治時期了,一待就是十年,等到蔣經國死了,新的政府卻不敢過問這些孤軍二代的身分,成為沒有護照和身分證的無國籍人,當時,我還在報社服務,也因為這個事件認識了楊和鄭,一起為他們的人權奮鬥著,現在還可以想到那些年四處綁布條,到處抗議的日子,這些辛苦總是沒有白費,楊和鄭可以獲准離境,所持的護照是一次可以使用的護照,到了馬來西亞機場以當場結婚的方式入境,三年後歸化馬來西亞,成為馬來西亞人,我還是這場婚禮的見證人,現在想起來如是昨日。
有些人生的無奈是可以以奮鬥來解脫的,但是有些無奈就不是以一人之力可以解決,那是歷史和地球的共業了。
楊在信末中說雨林中沒有網路,所以他可以重拾已經荒廢的鋼筆,倒是我,收到這封信和那株乾燥花的香味時,心情彷彿回到雨林了,但是這些年一直在電腦的鍵盤上打滾,似乎已經忘了如何提筆寫信了,看來這也是現代人的無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