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是近年的顯學,媒體上不管是報紙、廣播,還是電視,總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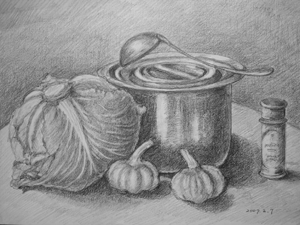 時在報導著何處有什麼美食,如何如何的美味。作家也流行談吃,寫文章、出版飲食書;不會吃不懂吃的人儼然落伍了。
時在報導著何處有什麼美食,如何如何的美味。作家也流行談吃,寫文章、出版飲食書;不會吃不懂吃的人儼然落伍了。
有個朋友一方面揶揄現代人是不是回到「口腔期」, 一方面就說她簡直有了「美食焦慮症」;讀著、聽著別人甚至專程去哪個城市的哪一個餐館吃了某一道食物,開始以自己的「驚訝」和「不懂得吃」為異了。
我也是不懂吃的人,有一次文藝界的一日遊回來,自嘲只關心食物的朋友問我飯好不好吃?我說還不錯,她笑起來,「幸好我沒去。你說還不錯,那一定很難吃。」都說富過三代才懂得吃,我們家連一代也不曾富過,不懂得吃顯然不是我的錯。
大約我的味蕾比較遲鈍,一起吃飯時有人說某一道菜用某種香草做佐料才有這種「幽微」的香,有人說某道菜至少燉了五個小時,味道才如此恰到好處,進一步判斷今日廚師的心情一定不錯云云,都讓我佩服。更厲害的還像寫文章那樣的說第一口讓她的味蕾甦醒過來,第二口讓她回味到某一年某一日的情境,第三口就讓她有了戀愛的感覺。電影〈芭比的盛宴〉裡的菜能讓枯木逢春,有情愛有情色的神奇效果,不料我的生活周遭也有類似功能的味蕾,和心靈。
我倒也不是不曾吃過精緻美食,當下美妙的滋味可以從舌頭緩緩流竄到腦門,可既無法精確描繪它的殊勝之處,過後更無法像朋友那樣回憶它們的色香味。
就說去年夏天吧,一個少說已富了兩代的朋友請了七八個人老遠到山上一家有名的店吃晚餐。本來還在想著吃頓飯何必花那麼多時間在交通上?可一進門,大家就嘖嘖稱讚。
那餐館有日式的清雅,也有中國的禪意。紙燈籠,榻榻米,厚實的老木長桌長椅,牆上錯落懸掛著大大小小的陶盤;地板上還有枯木和松枝的造景,教我回想到在日本京都吃湯豆腐的經驗。喝了茶後開始上菜了,食器都是陶質的,方的、圓的、三角型的,色澤也多樣,先就有了視覺美感的享受;上每道菜時,穿棉布衫的年輕女主人說明它的內容,繁複的烹煮工夫,以及最能品嘗真味的吃法。很多菜都很美味,可我已記不得吃了些什麼,只有在朋友拍下來的幾張照片中看得出有花生豆腐、桂圓米糕、生魚片,而綠色菠菜泥糕渣盛在小石臼般厚重的食器裡太美了!更講究的是陶盤上舖排著花瓣、竹葉或小花小草,有一葉山蘇上還擺幾個紅紅的果子;根本就像插花課嘛。而且,在我們的談笑晏晏中有古琴音在空氣中流動。
從燥熱的市區進來,一頓飯從日落吃到了繁星點點夜涼如水。
大家心滿胃足,優閒聊天不捨離去,有人下評語,「我們品嘗的不只是美食,還有友誼和文化。」「台灣話說的,吃氣氛的啦!」
對我來說,氣氛,以及美麗而樸拙的器皿,比食物本身令人難忘。
這也因為我習慣淡食,對於食物一向不苛求的緣故吧。
每次去買菜,我一定買兩斤番薯葉──如果沒被買光的話。回家後例行的儀式是挑去老莖,攤在報紙上稍微晾乾水分,再分成四包冰起來。每次燙一包兩個人吃,蘸醬油或淋和風沙拉醬,竟然也常年吃不厭。除了幾樣據說要用油煎煮才有防癌或特別養分效果的外,其他青菜也都燙著吃。省事,也減少廚房的油煙。
孩子們回來的日子,餐桌上才有肉類,平日偶爾的葷菜只是魚。紅燒百葉豆腐、烤麩、豆干和各種新鮮的菇,倒是差堪比擬為肉了。
有趣的是,描寫美食的文字和圖片,總是比實物更能讓我口角生津。是文字給人更多遐想的空間,還是要怪我見識不廣又不聰敏的味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