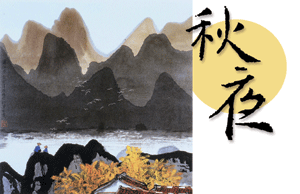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過客。」白驕過隙般的人生幾十年光陰,更是短暫。任何妄想永恒的企圖,都只會無端增加自己的煩惱。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過客。」白驕過隙般的人生幾十年光陰,更是短暫。任何妄想永恒的企圖,都只會無端增加自己的煩惱。
初秋的背影漸行漸遠,成了昨天的記憶。人跡板橋霜,深秋的腳步聲逐漸清晰起來了,讓人真切感覺到萬木蕭條的寒冬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南國山水的變化還不太明顯,北國原野上的樹葉已經由翠綠演變成淺紅,不久又會由深紅演變成金黃,乃至枯萎墜落。
玉露雕傷楓樹林,這就是自然的力量。
秋風一起,悲秋的歌賦就多了起來,彷彿這是一個天生惹人悲傷的季節。假如有人真的相信了這一點,那就錯了。悲秋其實是文人的自戀型態,是騷客的無病呻吟之舉。當然,劉禹錫「我言秋日勝春朝」的判斷又矯枉過正了,也不好,過猶不及。還是醉翁說得好:「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秋天和其他季節一樣,是一年中的一個特殊時段,有著與眾不同的個性。它一頭連接著盛夏,一面通向嚴寒,把冰火迥異的兩者協調起來,帶給人們一個舒適的季節。秋天不但氣候舒適,而且還伴隨著豐收的喜悅。春種秋收,當人們捧起自己辛勤耕耘的果實,心情充滿喜悅和快樂是自不待言的。如此說來,秋季給人們的感覺應該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季節。文人悲秋還有一些原因,就是借此寄托一種悲憫情懷,或者標榜清高而已,人們聽到之後千萬不要人云亦云地哭天抹淚。
雖然不少文人喜歡悲秋,但是像李白這樣具有曠達疏放胸襟的人,對四季輪轉就很看得開。「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過客。」萬物之於天地不過是過客而已,白駒過隙般的人生幾十年光陰,更是短暫。任何妄想永恒的企圖,都只會無端增加自己的煩惱。
人生也和季節一樣,有著自身固有的運行軌跡。在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身上仔細觀察,也會發現死亡的命運伴隨著誕生已經注定。悲觀者看到這一點,可能會涕泗橫流,傷悲不已。而樂觀的人發現之後則會把精力放在如何使人生更加輝煌燦爛上,而不去徒勞的哀怨。「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夫子在這個問題上就很曠達,把「聞道」置之於生死之上,這樣一方面擺脫了對未知世界的恐懼,一方面使精神有了寄托,用「聞道」的求索來充實內心,充實生活,內心的蔭翳一掃而空,於是充滿了陽光,自然就不會有悲從中來之感了。不是經常有人說,「幸福是什麼?其實就是一種感覺!」精闢之至。
當然,人人都有欲望,只要人們能夠把這個欲望「圈養」在一個許可的範疇,它還會成為人們奮發的動力呢。被千百年來奉為聖人的孔夫子也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就是境界,這就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的聖賢胸懷。
我等凡夫俗子不可能修煉到這種崇高的境界,但是可以做到享受生活,用感恩的心情對待自然的賜予,對待親情、友情,對待承載我們思想的身體,對待手頭的工作,有了這番心境,就會用微笑回應不如意,「不怨天,不尤人,」保持一份秋水般寧靜的心情。也許你沒有能擁有內心深處所渴望的地位、財富,但是可以擁有快樂。因為實現獲得地位、財富的目標要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所影響,需要機遇的援手,非憑藉自身能力完全可以駕馭。但是快樂的閘門卻掌握在自己手上,只要人們願意就能夠得到。對待財富是這樣,對待生命也是如此。人們雖然不能使自己身體永恒於天地之間,但是卻可以用自身的思想光輝照亮後人夜行的山路,從而達到永恒的巔峰。
自然的季節也好,人生的「季節」也罷,任何一段都會有無可比擬的精采之處,只要懂得欣賞,秋天的菊花和春天的蘭花一樣燦爛,一般高雅。
寫到這裡,想起了東漢詩人宋子侯的〈董妖嬈〉,其中桃花的自白相當精采----「秋時自零落,春月複芬芳。」試想,假如懷有這樣拿得起放得下的胸襟,那裡還會有煩惱和憂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