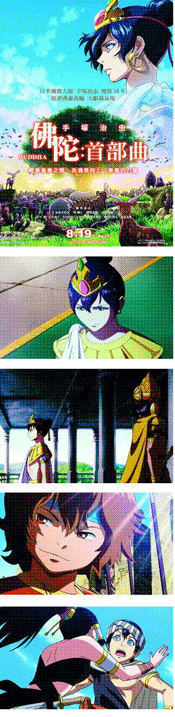
佛陀修行成佛的故事,在中西方藝術作品中幾經改編,他的盡棄富貴榮華,為了解圍牆外那一真實殘缺的世界,尋找其中「必然有我能做的事。」
這樣的生命探索,啟發了如德國小說家赫曼赫塞的《悉達多求道記》,將主角取上與佛陀一樣的名字悉達多,藉由他的流浪、沉淪、掙扎和悟道,思考自人類歷史開始反覆不止的爭戰殺戮、弱肉強食等等。或是由導演森下孝三改編自漫畫家手塚治虫原作的《佛陀:首部曲》,將焦點聚集在出走前,悉達多王子前半生的矛盾困惑,最終剃度走向人間。
電影大量刻描了悉達多出生的釋迦族所處國家的局勢,長年面臨敵人的烽火進逼。為了守衛家園或擴張領地,以避免被併吞而戰事頻仍,士兵和更多的百姓在其間平白犧牲,連帶造成的貧窮或瘟疫蔓延,致使病老者在街頭等待死亡。
生、老、病、死,構成了人類從出生開始受難的一輩子,沒有什麼能夠逃脫其間。
就好像也沒有人可以逃脫穩固社會結構的種姓制度,將人類分作四個階級,婆羅門、武士貴族、平民和奴隸。
一個人的一生,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已決定,再也無法翻身。
人生的困惑與課題
悉達多,出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被修行人預言將是統治人間的王者,在成長過程中,即顯出悲天憫人的胸懷,見到狩獵會不忍,見到人的死亡會困惑,不懂何以生命會如此無常,更不懂,城堡圍牆外的世界,到底是如何?
直到遇見蜜凱拉,在她的帶領下走進「真實世界」,看到偷竊的小孩被群毆,看見老者橫死大街,一次一次動搖、困惑著他善感的心。
悉達多想了解外面廣大的世界而屢屢受阻,相對而言,電影透過奴隸查普拉如何隱沒身世,逐步攀爬至一國最榮耀的武士位置。兩個人在身分階級的龐大規範下,無法超脫卻思索超脫之道,因此痛苦、疏離。
兩人在戰場上交手,只因悉達多身穿君王之服而奔前刺殺的查普拉,卻在最後一刻從悉達多明澈雙眼中,看見一個超過階級、身分、象徵的目光,彷彿被洞悉一切而止步於前。其後不久,查普拉便為了救出繫獄的母親,被揭發奴隸身分,而被賜死。
像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悉達多穿過大片戰死的骸體,踏過所有忠臣,認識或陌生的臉孔,不解人何以為了戰爭而殺害異己,甚至只是一隻無害可愛的小獸。
尋找生命的答案
身在榮華之中,卻思索著外面世界充斥的貧窮,歷經蜜凱拉為自己所受的極刑,歷經不可理解的戮殺和死亡,終於決定放下一切,悉達多自問:「一定有什麼是自己可以做的,為了那,我願意拋棄一切。」將王冠還於皇宮,將盔甲飾物歸於母后父王,將一頭長髮歸給妻子。只剩一件披衣,走出王朝庇蔭,走進世間的祕林,「等找到答案,我便會回來。」
悉達多為戰死荒野上的過去敵人的眼睛闔上,像與過去和解,從今以後是流浪之途的開始。
《佛陀:首部曲》反覆呈現著人類殺戮爭戰的根柢,有一幕,一位修行人為了救中毒的查普拉,讓許多獸族接力奔跑至喜瑪拉雅山上尋找解救處方,卻被長老怒責,為了救一個人,害多少馬匹、豹、鷹鳥力竭而死。修行人因此被責罰終身為獸,放逐野間。
佛陀想的不只是人類的和平,更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和諧,就像祂出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那是屬於天地之間萬物的和睦幸福,如果只關心人類利益,則爭戰一日不可能結束。同樣,也唯有想著,「一定有什麼是自己可以做的。」如此,才可能超脫若干不平現象,為自然界的各種生命沉思、著想。
悉達多修道的故事千年流傳,然而戰爭卻恆長不止,這或許便是人無法超脫自身設制的各形式階級,以及為權力欲望而擴張的根柢,但踏在荒土上,卻仍有人為某個遙遠的改變,拋下一切,踏上流浪者之途。
世界的改變,有悉達多能做的事,因此,也必然有我們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