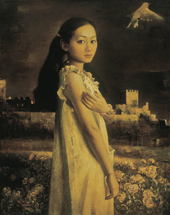 在眾人目光尚未聚集之前,踏入車廂的瞬間我已經發現她的存在。頭倚靠著窗外流過的萬家燈火,像反覆搜尋大氣中電波頻道的人形收音機,口中沙沙吐出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語句。
在眾人目光尚未聚集之前,踏入車廂的瞬間我已經發現她的存在。頭倚靠著窗外流過的萬家燈火,像反覆搜尋大氣中電波頻道的人形收音機,口中沙沙吐出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語句。
如果不發出引人注意的喃喃細語,她就像平日隨處可見的都會女子,有點年紀但保養得宜,一頭烏亮的長髮如蛇盤踞腦後,穿著剪裁大方的深色套裝,耳垂上咬著CHANEL耳環,上頭的雙C字母隨著站與站之間的停頓而晃動。然而,下班時分和巨大疲累一同壅塞入車廂內的男男女女,大多無視女人的自語,彷彿集體陷入凝滯的夢境中,而後在車門吞吐的瞬間突然清醒,雜沓紛亂的離去。只有我清楚聽見像是在和某人對話般,在長長地嘆氣後她再度開口:「……人家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幸好他不會這樣對我。」一邊打開腿上的提包拿出口紅與鏡子,一如登台前的女伶,仔細挽一挽鬢邊掉落的髮絲,反覆對鏡塗抹口紅。
我豎起耳朵聽見:「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一句尚待解碼的暗號,準確地傳送到我的基地。究竟這是一則都會愛情故事的結論?還是佯裝瘋子的智者對世間男女的一句警語?或是我正目睹一個孤獨心碎的女子邁入瘋狂的過程?但實際上,真正的瘋狂愈來愈難以指認,這個城市的人們難耐寂寞,獨自一人時習慣通過各種電子通訊在虛擬的空間中呼喊他人,向遙遠的星球發出訊號。起初我總以為那些邊走邊對著空氣說話的人、低頭看著手中螢幕傻笑的人、打開電腦在各處遊牧的人,是最寂寞的。後來我才明白那些坐在井裡頭,自己和自己說話,自語久了以為似近又遠的回聲是他人,才是真正寂寞的人。寂寞到極致,內心的黑洞不小心開啟,一併吞蝕周遭四散的星塵。
車過劍潭,軌道的下方是隨著夜色逐漸沸騰的市集,人潮湧出又湧進,浮盪不定。女人再度抵著窗,望著遠方。她在看什麼?隨著她的視線望去,台灣欒樹乍黃轉紅,已是秋天,再遠一點穿過層疊高樓後是暮色裡的淡水河,再更遠一些是躺臥未眠的觀音。她什麼也沒看見,招牌霓虹閃爍刷刷畫過眼前。過圓山不久,車如龍潛入地底,漆黑。
我繼續聽見她含糊咀嚼話語,再一次打開提包,拿出一罐上頭印著小護士圖樣的軟膏,而後忽地抬起腳,用擦著鮮紅指甲油的手指緩慢地在腳底板上塗抹藥膏。薄荷味漫開,周遭的人們終於注意到她奇異的舉止,高跟鞋跌落腳邊,一位穿著高雅的女人正撩起裙襬在捷運座位上翹著她的腳。比想像中更為肥白的雙腳上同樣塗著明艷的蔻丹,腳底卻令人吃驚的骯髒,和潔淨近乎完美的外表全然不相稱。乍看一片灰撲撲,而上頭龜裂的痕跡深淺不一如渠道般漫開,黑色的汙垢嵌入其中,最深的一道正張開紅色的小嘴喊叫,並無聲痛著。
而她依然在自己的世界裡說話,一邊用白色的軟膏來回餵食那傷口。
原來這一路上,我不只是接獲了她發出的孤獨訊息,而是在某些不經意的時刻裡,闖入了她內在的房間,拿起她刻意遺留的鑰匙,想要一探究竟,打開門卻見一片斷垣殘壁。這才明白人生不是一襲長滿蝨子的華麗衣裳,而是無意間翻至反面,發現精美織功的背後滿布纏繞難解的千絲萬縷。那是她生命的背面,用傷痕處處黑汙的腳底告知我的一則秘密。原來,最深沉的寂寞或悲傷無法用言語來表述,但身體都知道。
車廂內人們開始嗡嗡地低聲討論,突破了女人用自言自語打造的私人空間。女人收起軟膏,重新拿出口紅,在被眾人眼光、耳語圍剿的時刻來臨前,她維持僅有的優雅,再度補妝。車停,台北車站,撐起傾倒的高跟鞋,她像條蛇從人潮的間隙滑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