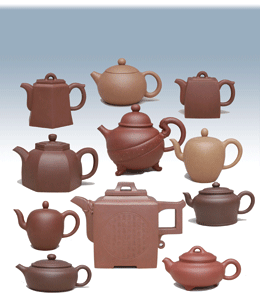
己丑暮冬,留聲先生命寫「潘氏紫砂」四字,說是為宜興製壺高手潘華兵先生索書。寫字有人賞,雖不能換酒嘗,不免一番自我陶醉,也就欣然敷紙。幾天以後潘先生捎來一把紫砂壺。
把玩在手,這壺造型明快有力,神韻古樸又不失典雅,做工精細,線條凝煉圓潤,儼然名家手法,落款卻非「潘華兵」,狐疑之際,方知潘先生並未以自家款銘問世,而是純代名家製壺,款是名家的款,市價自是不菲。為此我走訪宜興,徵得華兵先生首肯,以代工的價格,落自家的款,參與二○一○年吳江台協婦聯慈善義賣,潘氏紫砂的審美情報,贏得青睞,深獲好評。
《陶庵夢憶》說崇禎戊寅年,張宗子訪南京較老子論茶,啜茶即知產地與製茶時節,令較老子咋舌稱奇,兩位高士瀹茶,用的正是有益助茗茶之醇郁芳香的荊溪壺了。而這位生長於華貴家庭的官宦紈子弟,甲申之前沉溺聲色犬馬之好,茶淫桔虐自不在話下。品茗論茶用紫砂壺亦屬必然。祇是明朝亡後,宗子先生不作順民,披髮入山駴駴如野人,窮困潦倒而志在明史,有別於甘為清室鷹犬的二臣,令人仰望。
何以這盈把小壺,明清之際,不僅是皇室貢品,也是公侯將相乃至販夫走卒的日用器物,更是詩人墨客把玩文物?早在宋代即已傳誦紫砂壺,逮至大明正德年間龔春(供春)因手工精湛,宜興壺聲名更著,再傳弟子時大彬與文人雅士切磋品茗與壺藝,以高超製壺技藝,化大壺為小壺,更融入文人雅致品味,造型多變,承先啟後的時大彬壺型簡捷質樸,胎息著濃濃的藝術美感,就連其入室弟子徐友泉,晚年也感嘆:「精工製壺卻不及先師拙樸的耐人尋味。」無怪乎時大彬尊為「壺聖」。
乾隆年間宮廷直接製紫砂器具,陳鳴遠等名家輩出,溧陽縣令陳鴻壽自創壺式請名家製壺,親自雕雋詩文,文人與名匠共構「曼生十八式」名壺,也使中國藝術文化豐富獨特。不幸太平天國興兵與清軍在宜興戰爭,陶都破壞殆盡,邵大亨等少數人苦撐壺藝,紫砂壺雖命如懸絲,巧奪天工的技藝不絕。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商人開拓外貿商機,繪圖仿製古代名器,造就不少名家,俞國良、馮桂林、汪寶根、吳云根、蔣燕亭、裴石民、王寅春、顧景舟、程壽珍、朱可心等紫砂大師皆是一時之秀,顧景舟更是個中翹楚,紫砂壺的鬼斧神工代代傳承,是人間瑰寶。
小說紅樓夢寫到櫳翠庵茶品梅花雪,妙玉烹茶,便斟了一斝遞與寶釵,斟了一盉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未必找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原來妙玉的清潔高雅,茶具自是不俗。不俗也正是宜興紫砂壺最引人入勝處。
名家茗壺匠心獨運,線條曲直變化存乎一心,展現的造型多一分則平庸,少一分則俗氣,輪廓講究和諧端莊,這需要紮實的底蘊與深厚的美學修養。壺聖時大彬與文人過往甚密,就為紫砂壺注入濃厚的文人氣息了,明清迄今此風依舊。
潘華兵師承顧紹培大師,並追隨徐泉元先生,潛心壺藝,又是馮桂林大師外孫,以方壺著名,當知氣勢渾厚,線條流暢,質感溫潤方是壺外神韻。喜見先生方器醇厚飽滿,又有圓器的靈秀,他日有幸,更願見先生開創自我風格的精緻作品,展現元氣淋漓的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