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擴張與壅塞 :四奇士合唱團〈討厭的公共汽車〉
記得小時候曾經偶爾見到這樣的老式公車:它們多分配於前往故宮外雙溪的213路線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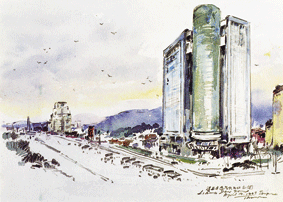 次,或是台汽中興號一般市區通勤路線。它那源自排氣煞車系統的獨特煞車聲,前面引擎「噗嚕噗嚕」直響,加上後頭排汽管經常發出類似連珠砲聲,還有在行車當中不時傳出的氣櫃放氣聲,每每令人印象深刻。
次,或是台汽中興號一般市區通勤路線。它那源自排氣煞車系統的獨特煞車聲,前面引擎「噗嚕噗嚕」直響,加上後頭排汽管經常發出類似連珠砲聲,還有在行車當中不時傳出的氣櫃放氣聲,每每令人印象深刻。
後來從一些書上老照片才知道,原來這可是早期七○年代曾在台北流行一時的罕見「賓士」中型公車(Mercedes-Benz LP1113B),當年(一九七四年)由台北市公車處首度引進,據說該車型由於既是「賓士車」名牌,車廂上又裝有冷氣設施,故曾一度引起民眾搶搭。此後,各業者紛紛跟進添購冷氣車,不久便全面取代了其他普通車,成為現今公車的標準配備。
眼前又一天過去了,城市本身或許不會在乎我們,而我們,卻渴盼聽到城市的聲音,並希望據此追尋它最初原始的淳樸本性。
人在公車上,車身不停搖晃、眼前景色一秒秒變異,慢慢從點延伸成線、擴展成面,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氣味不斷在身邊流轉。哪怕貫穿南北還是橫越東西,自己旁觀著他人上車又下站,終也有一個目的地。到站了,終究得要下車。
於是乎,每當你我與那些行色匆匆的都會男女擦肩而過時,昨日一切彷彿就在身邊,只是帶不走,掉在地上,便成了回憶。
回溯起過去中學時代仍需搭車通勤的往日歲月,大街上總有公車過站不停,或是過站才停,然後把車停得老遠,眼見眾人追趕公車幾乎成了彼時每天習以為常的戲劇化活動之一。
話說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精神本質就是掠奪。
現代通勤族在尖峰時刻搶搭公車,其景象宛如整個社會競爭的具體縮影:有的慢條斯理、有的眼明手快,有座位的、沒座位的,有人謙然讓座、有人旁若無睹。儘管,我們也許不想跟這城市有太親密的連接,甚至可能覺得自己根本不屬於這城市,但最終卻又都只能心有不甘地追逐著它的步調節奏,一如六○年代風華正盛、來自台北三重埔的男聲「四奇士合唱團」娓娓唱詠著業已消聲絕跡的〈討厭的公共汽車〉(明文作詞/黃茂雄編曲/一九六四)這首台語歌調:
透早出門心輕鬆,沿途唱歌手搖動,看見辦公時間到,大步用走無越頭,彼時拵公共汽車,闍好也來到。
趕緊走來車門前,誰知客滿車無停,搭車的人排歸陣,車擱無停上介害,總也著暫時忍耐,繼續來等待。
辦公時間真寶貴,搭無汽車上克開,已經等了半小時,全無看見車到位,到底是為著啥代,汽車朗不來。
搭車眾人塊議論,比較行路有恰輸,恐驚時間趕沒付,大家忍耐綱若龜,討厭的公共汽車,全無同情阮。
現在時間八時半,無去辦公欲按怎,公司人人會講起,大概厝內有代誌,實在是搭無車班,明明氣死人。
看著汽車來到位,大家趕緊塊相擠,彼時車掌發脾氣,叫阮後班即扒起,只有是目啁金金,送車開行去。
探究歌曲背景所在的六、七○年代,正值台灣中南部農村第二代透過教育制度體嘗城市摩登生活、晉身白領人口面臨空前快速發展的過渡期。在這裡,所謂城市的姿態,其實就是擴張。發展到今天,人們已經無法擺脫城市的奴役。不管你樂意不樂意,都得接受,就像是歌詞裡趕赴清晨上班久候公車多時卻搭不上的主人公感歎:「總也著暫時忍耐/繼續來等待;到底是為著啥代/汽車朗不來」。面對無可改變的巨大現實,恁憑個人微薄之軀也只得莫可奈何地揶揄自嘲:「討厭的公共汽車/全無同情阮;實在是搭無車班/明明氣死人;只有是目啁金金/送車開行去。」
相對於絕大多數作為供養這城市運轉的基層底蘊的人們來說,似乎唯有不斷地更換姿勢、轉移壓力,才能繼續留在城市裡的某一角落。如是,在慌亂的擁擠當中,我們彼此寬容,並且使勁地縮小自己所占的空間。
時下面臨城市發展與生存的艱難,身為小市民一分子,能每天按時擠公車,大抵也算是當下幸福生活的一部分了。
隨著黑膠曲盤緩緩攸轉,郭金發的磁性低音、林春福和賴謙祺清亮的中音,以及陳木乾脆俐落的高音,共同交織成「四奇士合唱團」獨特而細膩的參差聲線。在詞意內容上,〈討厭的公共汽車〉雖表面透露出一個都會白領每日汲汲趕赴上班通勤的匆忙與懊惱,但值得玩味的是,此處的旋律節奏卻是湧現著一副晃晃悠悠的詼諧腔調,庶幾近乎一種超慢速地搖擺前進的安逸氣氛,悠然而自在,彷彿直欲將六○年代台北城特有的生活氛圍用聲音給永遠定格下來。
從城郊衛星鄉鎮前往市區中心,三重、蘆洲、新莊、中永和、板橋,熟悉的公車路線穿越過河堤旁的幾條舊街,上橋。橋上風景如昨。那看不盡說不完的曲調故事裡,承載著無數台北人的悲愁歡笑以及點滴過往,歌聲中有他們的人生,也有我的人生。
註一:張愛玲,一九四三,〈公寓生活記趣〉《天地》月刊第3期,上海:天地出版社。
註二:夏宇,一九八四,〈墓誌銘〉,《備忘錄》,自印出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