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渡,在初秋的河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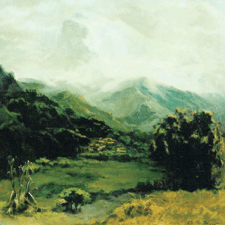
河殤,在颱風眼皮底下。
滑著橡皮艇與膠筏,舟中人不搖櫓、不戴笠,焦心穿梭,擺渡的眼眸望穿這該死的秋水,凝睇這百年罕見的河殤景象。嘴裡幽幽唱著新寫的歌詞:秋八月,風雨已至,伊人泣斷了弦歌。
我們的島,沒有騎馬流浪的遊牧民族,只有依根而眠的原鄉人。漂流,該是什麼樣子?
秋八月,一場破世紀的颱風自東方盤旋而來,風神雨神大展神威,連山神樹神也不禁懼怕了,一一屈服在它的淫威之下。昨日,這裡還是綠樹參天,翌日,綠樹滾到了太平洋,漂流,再漂流。樹在河岸邊,在水之湄,在海口地,隨著海浪跌跌撞撞地散了又聚,聚了又散,人們管它叫漂流木。漂流又是什麼樣子?問我,我沒有答案,我只是一個疑惑者,疑惑天地的運作,疑惑一棵樹的歸處,甚至疑惑有情與無情天地的界限在哪裡。
八月的秋風方起,往東拂過,落在原鄉人深邃的臉龐。彼時,豐年祭的舞蹈才剛開鑼,山谷間本該迴盪著高亢的族語之歌。那是最動人的山歌,因這一片最翠華的樹林。他們有了靠山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有了豐收,也有了歡唱的舞蹈。
地表上從未出現如此駭人的颱風,一夜醒來,山頂的樹已經躺泊在山下,失去根,失去葉,只有在嚴冬才光禿禿的樹呀,裸身在海洋。
漂流是結果,也是起始。
不能移動的植物來到了海邊,誠如河伯遇見了北海,生命的天旋地轉過後,該問問,這裡是天地的哪一方?
一個男人,他跪在海邊,飲泣,他的房子掉進太平洋,成了海龍王的祭品。
一個女人,她徘徊在河洲,哭號,她的夫君憑空消失,化為無蹤無影的失聯人。
西風還未肅殺了這土地,東方的風雨就趕赴上空對峙,鏖戰,不過是兩方相殺,不過是遍野狼藉,歷史記載得很詳盡,促使山河破碎的,可以是兵荒馬亂,可以是韃子入關來,也可以是暴雨馳騁氾濫。
無法停止漂流,這裡是大海。一群木頭無由地來了,東晃晃又西晃晃,像個可憐無助的孩子離開了靠山。昨日,樹還在山巔俯瞰人間,隔日,卻必須沉浮仰望著山林的故鄉。本不該遠遊的,因為臨行前尚未話別,本不該遠渡的,總以為自身一生都不會離開。
千年之前,莊子說話,秋天一場大水把黃河氾濫了,壯闊的氣象讓山谷驚變,河伯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它來到北海,遇見了北海之神,海神告訴了河伯:「百川啊,你永遠的歸宿是大海。」當年的水撞見了無邊的煙波浩渺,恰似遊人回到了淵源的家。
河水回歸了,那麼山呢?樹呢?無根地晃盪著,在海中猶不忍離岸太遠,至少,還能遠遠望山。
一群人,他們身無分文逃離了依偎千年的山,寄宿在偌大的宇宙一角。他們的眼中凝結了恐慌,曾經傳誦千年的綠水千山怎麼變了樣,錯得好陌生。
流浪的第十天,他們擦乾眼淚,決定不再哭泣,他們在偶棲的一隅唱著〈那魯灣〉,陪伴著一代又一代的原鄉人,歌聲依舊美好,他們的曲兒仍充滿了濃濃道地的原鄉味,依舊引人入夢來。山崩過後,狂風暴雨奪走一切,卻搶不走他們唯一的食糧,只要原鄉人還在,這天地就會繼續存在著曼妙的歌聲。人們是如此堅定相信著,旁觀的眼灼亮期盼著,原鄉人不屬於漂流的宿命,因為他們的名字裡沒有流浪,聽聽「原住民」這極好的名,就得認清流浪不是他明天的方向。
木已漂流,成了遊牧一族,但這裡可不是蒙古大草原,我們的原鄉人不願失根,縱橫千里,他們只想尋著一座山,一個靠山。流浪的第二十天,他們或已覓著未來的家鄉,或仍在尋根的路上徘徊。然他們的淚痕已乾,瞳孔裡漸漸露出了曙光。我也開始懂了有情天地的界限在哪。
水滴奔向大海,是有情。人不願離根,是有情。那青青高樹落難,成了漂流海洋的木塊,即使離開,也要仰望著出生地,仍是有情。
「我們不想離開家鄉太遠,就算遷村,也要在附近,才能看見故鄉。」原鄉人的血液裡,從未流著徙人的基因,不知漂泊的味道,也不想淺嘗,他們對著山林輕聲低吟:「等我,我一定回來。」
無情天造訪有情地,舉國譁然。寶島的特產有稻香,有茶香,除此之外,可別忘了還有熾愛土地的原香。被水沖過的地貌很陌生,不再是熟悉的模樣,一群人,背上馱著沉沉的米袋,逕往深山裡鑽去,再鑽去。他們望著新墾的原野高山,停下腳步,放下了米袋,指著森林。手指的方向將是未來安枕的夢土,一座穩穩的靠山。
不想當異鄉人,過去不是,未來也不是,這一次是最終一回遷居流浪異鄉。
攤開寶島的地圖,手指頭點了點幾個地名,原鄉人問了聲:「可否安然扎根?永遠永遠安然扎根?」
沙灘上,羅列的漂流木堆成了一叢叢小山,它們沒有根,因為沒有根,樹木學會漂流。海很大,可它們只想依著泥土聽山歌,與原鄉人隨著徐風、伴著山間雲霧共呢喃。
擺渡過了一巡,明白了,河殤的疤將漸漸癒合,新鏟的泥土上,將引出流浪者落地歸根後新發的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