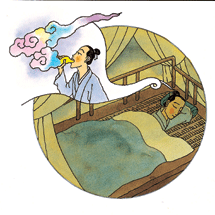
張迴年輕的時候刻苦寫詩,可惜沒有什麼成績。有一天夜裡,他夢見天空降下了五色雲。張迴伸手抓了一團雲,很快的把五彩雲吞進肚子裡。說也奇怪,從此以後張迴寫詩的功力大增,很快的成為行家。(洪義男/繪)
有一天,張迴寫了一首〈寄遠詩〉:
錦字憑誰達,
閑庭草又枯。
夜長燈影滅,
天遠雁聲孤。
蟬鬢凋將盡,
虯髯白也無?
幾回愁不語,
因看朔方圖。
張迴帶著作品去拜見齊己,齊己邊看邊點頭,還不停的吟誦。他稱讚著張迴的作品,並且建議把「虯髯白也無」改為「虯髯黑在無」。
張迴聽了齊己的話,就拜齊己為「一字師」,這也就是「一字師」的由來。雖然古書上這麼記載,但是仔細一看,齊己把「白也」改為「黑在」,應該是兩個字,而不是一個字。然而,也有只把「也」改成「在」的記載,「一字師」的名稱就這麼流傳下來了。
名詩人鄭谷住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齊己帶著作品去拜見他。齊己在作品〈早梅〉中寫著:
前村深雪裡,
昨夜數枝開。
鄭谷看了以後,笑著對齊己說:「梅樹上已經有好幾枝開花,這就不能算早了。如果把『數枝』改為『一枝』,不是更好嗎?」由於題目寫的是「早梅」,梅樹枝只有一枝開花,才能表現出「早」的特點。
齊己聽了恍然大悟,非常佩服鄭谷的見解。從此以後,大家就把鄭谷當成齊己的「一字師」。
元朝的薩天錫有「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的詩句,山東有一個老者把「聞」改為「看」。薩天錫就請教老人為什麼要這麼改?老人回答說,唐詩有「林下老僧來聽雨」的詩句。
有一個叫乖堐的人,他寫了「獨恨太平無一事」的詩句,蕭楚材把「恨」字改為「幸」。這麼一改,立刻扭轉了詩的格局。
王貞白有「此波涵帝澤」的詩句,貫休把「波」字改為「中」,也是「一字師」有名的例子。
清朝東海地區有一個閨秀,她寫的〈藍菊詩〉中,有兩句是這麼寫的:
為愛南山青翠色,
東籬別染一枝花。
這兩句詩寫得很好,然而《巢林筆談》的作者龔煒,卻認為「別」字還有些不妥,建議把「別」字旁的「刀」刪掉,而成為「另」字。看,「東籬另染一枝花」,多麼別有意境、多麼令人耳目一新!
這個有趣的故事流傳開來以後,大家就稱龔煒為「半字師」,成為修改詩句的特例。
以上的例子,都是由別具慧眼的人,修改別人的作品。往往只更動一個字,就產生了點石成金、畫龍點睛的效果。不但得到原作者的認同,也引起了讀者的共鳴。
當然,也有作者自己動手的著名例子。宋朝著名的文學家王安石,他寫了一首絕句〈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
鍾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江蘇吳中地區,有一戶人家收藏了這首詩的手稿,只見稿子上第一次寫的是「春風又到江南岸」。然後,圈掉了「到」字,還在旁邊註明「不好」,把「到」改為「過」,接著又改為「入」,後又改為「滿」字。
王安石前後改了十幾個字,一字一字反覆思考、仔細琢磨,然後才慎重的敲定了「綠」字。這首詩不但成為修改的著名例子,也是歌詠江南地區的名作。
王安石的詩這麼一「綠」,就鮮活了一千年,再也沒有人能超越他。
北宋著名詩人黃庭堅,寫了:
歸燕略無三月事,
高蟬正用一枝鳴。
黃庭堅一開始寫的是「高蟬正抱一枝鳴」,覺得不是很滿意。於是把「抱」改為「占」。改完以後還是覺得不夠好,再把「占」改為「在」,「在」又改為「帶」,「帶」又改為「要」。經過反覆推敲、不斷吟誦,黃庭堅才決定選了「用」字。「高蟬正用一枝鳴」,就留傳到到今天。
現在,我們靜下心來,把王安石和黃庭堅用過的每一個字,嵌進詩句中,每句細念幾次、每一句相互比對。然後就可以體會出,王安石選「綠」字、黃庭堅選「用」字,就像在一局棋中,下了最關鍵的一個棋子,整局棋由於這一手而大獲全勝。
這種巧妙,如果能細細體會,對於文字的使用,應該會有意料之外的收穫。
半字師,可以是別人,
更可以是自己。
一字師,可以是別人,
更可以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