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道可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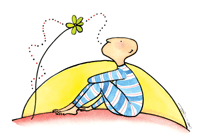
非常道。」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散文:蒙田和艾田
他不知自己一直在尋找這樣一個人,直到在宴會上遇見了艾田{1}。彷彿受到無形的強力吸引,他形神直奔艾田而去,為他吸收,並將他吸收。那麼熟悉、融洽,好像許久不見的老友,好像他們一直就在尋找彼此,好像在相識前便已相知。他說,艾田聽。或者艾田聽,他說。或者他們一起說,一起沉默。沒有一句話太多,無言也好。他們之間沒有勉強,沒有避諱,沒有隔閡。他對艾田無所求,也無所予。艾田對他也是。他們已不只是朋友,而是彼此的延長。他們是一個靈魂分住在兩具軀殼裡,相聚時便又合而為一。
四年後,艾田病死。
他跌跌撞撞,彷彿四下昏暗,一切茫然。他失去了自己,只剩一副冥頑的軀殼。直到他把要說給艾田聽的話傾注到文字裡,直到他開始嘗試一種自說自話的新文體:散文。
「我知道什麼?」他寫。
又寫:「知道怎麼死,便知道怎麼活。」
便一篇又一篇寫了下來,一直到死。
主題即是他自己。
詩:如米和山木
一件事發生了。之前,一切簡單完滿,他不覺得生活有所欠缺。之後,他覺得生活裡出了一個大洞,一片無法填補的空白。
那天,來了個陌生人,山木。他請他進屋,喝茶,問他從哪裡來,問他旅途上的見聞,種種問題,那些他自己經常沉思默想,未必是疑問也未必需要解答,帶著玄奧和神秘的「問題」。他一一回答,或者說,一一應和,有如影子回應陽光、樹葉回應微風、水面回應天空。他接續他的思緒,像一天接續日出。他填補他,像雲霧籠罩山巒,像河流充盈兩岸之間。在他面前,他沒有開始,沒有結束,他們構成了一個圓,沒有縫隙,沒有始終,沒有內外。他們陷入深談,陷入狂喜,日日又夜夜,無法停止,無法分離。然後,山木走了。帶走了自己,也帶走如米。
如米發現:早晨醒來,沒有他。晚上入睡,沒有他。屋裡沒有他,屋外沒有他。春來沒有他,雪來沒有他。思想開始的地方沒有他,感覺靜止的地方沒有他。空間裡沒有他,時間裡沒有他。他暗了,空了。他不是自己。不是真的。因為那無法填補的巨壑,那無法忍受的空缺,他開始寫詩,以文字捕捉曾經流過他們中間的音樂。
然後,山木回來了。坐在他的屋裡,一起喝茶、問答。他們再度忘我深談,陷入狂喜。好像不曾分離過,好像他們是落在一起的兩滴雨水。他們對坐交談,在果園裡散步,在院子裡仰望夜晚的天空。他們不是複數,而是單數,是一。
一晚,他們又像平常一樣對坐深談,門外有人呼喚:「山木!山木!」他便出去了,從此失蹤,永遠消失了。
如米的巨壑又再張開,他再次感到無比的虛空。他繼續寫詩,以文字捕捉他們間獨有的音樂。他從沒在文字裡提到山木,但山木充塞了字裡行間。
他寫:「不是基督徒,不是猶太人、回教徒,也不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蘇非教徒或禪宗教徒。不屬於任何宗教和文化系統。既非來自東方也非來自西方,不來自海裡也不來自地上,不是自然生也不是飄忽的靈氣,根本就不是由元素構成。我不存在。不是今世也不是來世的個體,不是亞當夏娃,也不是任何起源故事的後裔。我在無所在,我跡無可循。非靈也非肉。我屬於我的所愛,我見過兩個世界合一,呼喚那一個世界,知道而始而終,而裡而外,終究只有人類吞吐那氣息。」
以及:「春天時到果園來,那裡,在石榴花間有光亮、葡萄酒和心愛的人。你要是沒來,無所謂。要是來了,無所謂。」{2}
哲學:維根斯坦{3}
一件事發生了。將他灼傷,讓他眼盲。
他沒法形容,沒法解釋。他說不清楚,甚至,說不出來。語言完全無用。在那件事面前,在那一片白亮輕盈廣闊面前,語言像石頭,黑沉又且笨拙。
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首先,這句話的用字便有問題。發生、什麼、事酖酖這些詞都意謂了某種確實,可以拿時空來界定的,事件。然並沒有確切事件,也不在某個時刻某個地方發生。他有的只是一種感覺,一片記憶。不是獲得,而是失去;不是實在,而是彷彿。當他試圖把「那件事」托在掌中,呈現出來的只是空,是無。
而,無可懷疑,無可否認的,一件事發生了,一件重大無比的事,將他整個改變。之前他是一個人,之後是另一個人。唯一的根據是那感覺。忽然,遽然,在他毫無期待毫無防備的情況下,一切消失,或者,消失的只是他自己,他在一片無限開闊的空間裡酖酖不,不對,他並不「在」任何「地方」,毋寧是他「不在」任何地方,而那「不在」浴滿了光酖酖不,又不對了,並不是光,也不是暗,而是,而是,而是酘酘什麼?
不,沒法說,沒有適當、對應的語言。不是明暗的問題,不是在不在的問題,而是,而是一種無重,一種全然輕飄,一種脫離,一種飛翔,一種自由,一種無邊無際的快樂。而這些都不完全,不盡正確。他不能說是什麼,也不能說不是什麼。更像是全部,又像是空無所有。像得到了一切,又像徹底消失。他能說的,是他從沒有過那樣感覺,是他永遠不願失去那感覺。而在他意識到那感覺本身時,他已經還原了,從那感覺降落,再度沉重、黝黑、笨拙、不透明、不快樂。不,他不能說清。
而他想要說清。一試,再試,無數次。語言的混沌讓他氣餒,語言的無能讓他憤怒。語言所能做的,只是描述語言範圍裡的事物。而語言的範圍那麼局限,即使在那麼窄小的範圍裡,甚至都沒法做到絕對明晰。
所以,他得到的是兩個世界:語言以內和語言以外。那件重大無比的事,他發現,他完全無能描述,無法談論。所以,他決定將它歸於沉默。
也就是:「凡我們無法言說的,便當付諸沉默。」{4}
註:
{1}蒙田的生死至交叫Etienne de la Boetie,這裡取他的名以便和蒙田對應,儘管蒙田是姓。
{2}蘇非教詩人如米和生死交山木間的故事,最後兩段取自如米的詩。
{3}虛構的維根斯坦的經歷,取自簡娜‧賴文(Janna Levin)的《一個瘋子夢想突陵機》(A Madman Dreams of Turing Machine)裡的片段,稍加改寫而成。
{4}維根斯坦《哲學邏輯論》的最後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