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畫的行家也許不只一人郭恩慂,但他卻是唯一放下西畫之筆
佛畫的行家也許不只一人郭恩慂,但他卻是唯一放下西畫之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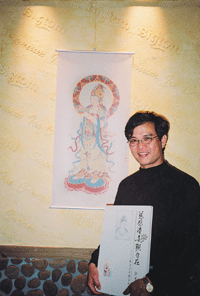 而轉向觀音畫作有成之人。三月開春,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將展出他的三十三觀音近作及耗時十五年的作品,精細的作品,由鉛筆打底稿、絹布白描、上櫃、設色,生動鮮活。
而轉向觀音畫作有成之人。三月開春,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將展出他的三十三觀音近作及耗時十五年的作品,精細的作品,由鉛筆打底稿、絹布白描、上櫃、設色,生動鮮活。
三十三觀音在佛教經典中有不同的化身及經典故事,「不論有多苦,我都會一直畫下去,畫好每尊菩薩像」,他要捨棄人世間的貪瞋痴,往一○八觀音畫作去努力。
出生高雄縣美濃鎮的他,小時候常見父親藝術界的朋友來家裡走動,但家中無錢可買文房四寶,更別提拜師學藝了。家鄉廟宇在興建時,畫師在牆壁上作畫,往往令他流連忘返;「那時我經常會拿起磚塊,把想畫的人物畫在水泥地上,想像自己也是廟牆上為菩薩彩繪的畫師。」
小學四年級,郭恩慂陪鄰居參加鎮上的寫生比賽,竟意外得獎。從此對美術畫畫有了高度興趣,校內校外經常得大獎,還得過全國美術設計優選。在台南高商廣告設計科念書時,郭恩慂陸續跟隨鄭時均、張添源、潘錦夫、朱玖瑩等前輩學習書法,也跟隨水墨畫啟蒙老師何仁先、楊智雄、蔡茂松等學習水墨畫。
一九九一年是郭恩慂很關鍵的一年,他看到董夢梅老師所畫的水月觀音,對工筆佛畫產生非常深的嚮往。隔年,他就放棄高中的教職,全心潛研佛畫。「脊椎坐骨神經疼痛,一整年都沒有收入,全靠太太扛起家庭重擔。全職畫家的艱辛,唯有走過的人,才能深深體會。」
董夢梅當時也對他說:「畫佛畫的人,如果腦海中充滿功利思想,是無法完成好作品的!」聽下這話,筆耕歲月,他經常將滿滿的感恩付諸畫作中,知足常樂,俗世的名利觀念,也慢慢被洗滌,成了淡泊的一身輕快。
一九九六年,他陸續畫了三十三觀音中的十幅作品,之後三年又完成另十幅作品,有如神助,繪畫時筆隨意轉、揮灑自如。「我常去植物園臨摹荷花,尤其受到敦煌壁畫、法海寺壁畫的影響,」他說,佛畫尤以法相的勾勒及線條功力最難,每畫一幅作品,必以最嚴謹恭敬之心,從打稿、定稿、白描、上框、設色,按部就班、小心翼翼,不容絲毫懈怠。
每幅畫的完成,至少得花上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記得畫琉璃觀音那段日子,我為脊椎疼痛所苦,一年只畫這張作品;畫多多羅尊觀音時,又出現恐慌症;畫岩戶觀音過程也遇到多重障礙……不過冥冥中,彷彿觀世音菩薩為我擋掉生命中的難關,安然度過。」
全神貫注在一筆一畫中,手畫佛、眼看佛、心想佛、口念佛、意念佛,心口意融在佛菩薩的世界裡作畫,所有紅塵俗世暫時拋開,那是一種至高的心靈享受。「觀世音菩薩有時也會有不可思議的顯現,但我皆以平常心視之。在繪畫時,感同身受觀世音菩薩慈悲為懷,念念相繼,成為我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
那一年,病中的母親正在生死邊緣掙扎,來自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力量,讓郭恩慂在畫延命觀音時,腦海中浮現準提菩薩的形象。他順應內心的靈感,將準提菩薩所持的法器與千手接引外相,應用在延命觀音畫作上,期能為眾生抵擋疾厄、延年益壽,屬於較「大膽」的創作。
佛教的故事裡說,人人心中都有一朵蓮花。在郭恩慂的三十三觀音畫作裡,幾乎每幅都有蓮花,諸佛菩薩多以蓮花為座,無論以何種形式呈現,蓮花都是溫柔佛心的綻放。
觀世音菩薩有時也會現忿怒身,給沉溺貪瞋痴的眾生當頭棒喝,使之猛然驚醒。「記得在繪畫阿摩提觀音期間,我也有過被『當頭棒喝』的經驗,後來放下執著意念,果然將觀世音菩薩慈悲聖容與威猛雄獅座騎靈活呈現。」
郭恩慂很了解,觀世音菩薩尋聲求苦,有求必應,其實在每個人的周遭,也到處是菩薩。在佛畫的過程中,唯有起滅不著相,才能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