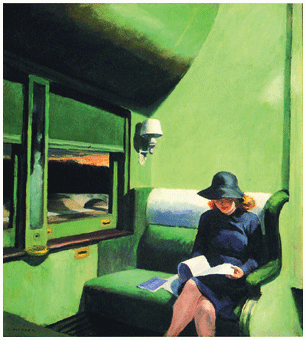
孤寂是一種心境,當這種心境被轉化為藝術的形式時,則會是一種具有驚人內在爆發力的攝人心力,而這種攝人心力,每每成為歷史的碑記,幾乎所有歷史上偉大的藝術巨匠都是這樣,都是孤寂生命瘠土中獨立奮出的種子,不畏風雨、不畏烈日,只為自己和人類掙脫困境,從深泥中艱難地探出芽苗,然後,成長、茁壯,最後成為一顆大樹,為更多需要休息的旅人,找到一處蔭涼、找到一柱依靠。
愛德華‧霍普(Edwand Hoppev 1882~1967,生於美國紐約),畫風寫實,但絕非照相的翻版;筆調靜宓,但遠離保守的古典幽雅;色彩沉穩,但已然脫去歷史或宗教繪畫的封閉。
他成長於十九世紀末,象徵現代文明的世界首都紐約,但他的作品中卻嗅不出繁華的喧囂,而是那繁華喧囂背後人類孤寂心靈中孤寂的影子。
如果現代文明是一種人為或人造的光,那麼,光照下的暗影,則是隨之而來的人類自己的孤寂心靈,霍普似乎提早喚出這份孤寂,讓它在畫中冷冷地站立,當人們的視覺一接觸到他的作品時,便將自己的孤寂,不自覺地從軀體的深處躍出,和霍普站在一起,共度這冷冷的時光。
「293號列車車箱c」的畫作中,繪一長途列車車箱的少婦,戴著寬邊圓帽,低頭翻閱手中的畫報,無聊的眼神無感地凝視著書頁中無聊的一角,閱讀只是一種藉口,更多的時間只是呆滯地凝視,凝視模糊的印刷體,凝視自己模糊的生命記憶,猶如列車快閃而逝的風景。冰冷的白色日光燈投射在到處漆著綠色的車箱內的四圍上下,更加深這份模糊記憶激起的孤寂感。
霍普的畫作內容極為簡單,一個孤立無援的人物,一把不知何來的巨大冰冷的光照、一大片幽黯的陰影隨形,而畫面中沒有任何一點激情,獨有一分霍普式的沉靜寂寥,或者一絲微細的呼吸聲。
霍普為什麼用彩筆畫這暗影孤靈?霍普為何不大肆舖張文明的喧囂樂土,卻選擇這肉眼看不到的人類集體孤寂意識的深沉呼喚?
是文明科技的動力愈快,人類精神孤寂和心靈的漂泊感愈形加劇?或者文明只能遮眼,心靈和精神的歸宿感才是人類真正的課題?
只有霍普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