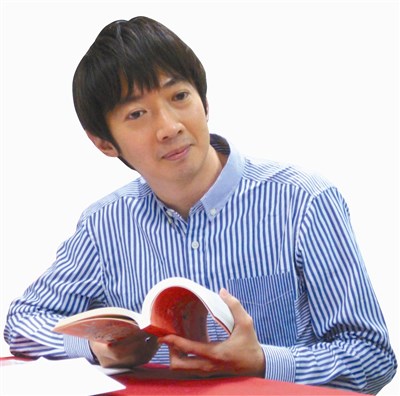 張維中 台北人,現居東京,任職傳媒業。大學時以長篇小說踏入文壇,迄今出版著作二十四部以上。小說與散文反映都會現況,內容多觸及家族議題、家庭再定義與組合的可能性。圖/聯經出版提供
張維中 台北人,現居東京,任職傳媒業。大學時以長篇小說踏入文壇,迄今出版著作二十四部以上。小說與散文反映都會現況,內容多觸及家族議題、家庭再定義與組合的可能性。圖/聯經出版提供 一青妙 父親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的長男顏惠民,母親是日本人。十一歲遷居日本。齒科大學畢業後,擔任牙醫師工作,同時兼顧以舞台劇、連續劇為主的演藝事業。圖/聯經出版提供
一青妙 父親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的長男顏惠民,母親是日本人。十一歲遷居日本。齒科大學畢業後,擔任牙醫師工作,同時兼顧以舞台劇、連續劇為主的演藝事業。圖/聯經出版提供 漥美澄 日本受關注的新人小說家之一,二○○九年以作品〈水分〉進入文壇,收錄此作品的《不中用的我仰望天空》一書,於二○一○年榮獲日本《書的雜誌》年度十大好書第一名。圖/聯經出版提供
漥美澄 日本受關注的新人小說家之一,二○○九年以作品〈水分〉進入文壇,收錄此作品的《不中用的我仰望天空》一書,於二○一○年榮獲日本《書的雜誌》年度十大好書第一名。圖/聯經出版提供 插畫/葉懿瑩
插畫/葉懿瑩
文/張映涵、杜晴惠
張維中:針對這兩本書(《紀念日》與《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進入我們的主題,飲食、料理和文學看起來毫無連結,但為什麼會決定寫到作品中?
一青妙:對我來說,我的第二本書《日本媽媽的臺菜物語》是想到我的媽媽,我的媽媽是一個純粹的日本人,她嫁給一個純粹的台灣人,結婚後就馬上和我父親一起到台灣定居,那時,她完全沒來過台灣,也沒接觸過台灣文化,更沒吃過台灣菜。到了台灣後,她以台灣料理、學台菜這件事,當作融入台灣社會的方式。當然,沒有人可以教她,她就找了父親一個會說日文的親戚,一個星期兩、三天到他們家,然後持續學習,之後就學了道地的台灣料理,像是:菜脯蛋、番茄炒蛋等。
漥美澄:《紀念日》這本書,一開頭就是描寫「三一一」這個事件,當時日本得到台灣很多資源,真是非常感謝。當時地震是發生在星期五,周六、日超市的食物被搶購一空,等到我星期一去超市,只剩一些乾貨,我在東京從沒見過這個場面。我有一個念高中的兒子,因為兒子是高中男生,食量很大,但是去超市沒東西買了,這件事對我來說衝擊很大,想到懷孕的女生或更小的孩子沒東西吃,我覺得很慌張,也因為這件事,我想到一個關於日本母親為了孩子的飲食的故事。
《紀念日》這本書,台灣還沒翻譯出版,故事中有兩個女主角,一個叫做「晶子」,出生在一九三五年的戰爭時期,十歲是小孩食欲最旺盛的時候,但因戰爭物資缺乏引發對食物的飢渴。另外一個女主角出生於一九七五年,叫做「真菜」,生長在飲食、物資非常富裕的日本,從小沒有餓過肚子,對於母親的料理有一點反感,我試圖在這本書裡描述不同世代,因為成長背景不同,無論飲食和成長價值觀都不一樣。
台式便當進日本校園
張維中:我對於窪美澄的這部小說印象深刻,像是她剛剛提到的「晶子」,在很貧困的戰爭時代,物資缺乏,沒有東西可以吃的時候,她跟好友對於吃東西這件事最開心的事,就是吃維他命,維他命吃起來甜甜的,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的生活經驗中,吃維他命讓他們有很愉快的體會,這是我們這個世代完全無法想像的。
我們都曾看過《螢火蟲之墓》(宮崎駿作品)這部動畫片,其實也有類似的情節,「糖果」在戰爭中是一個能夠滿足身、心、靈的一個飲食境遇跟情感之間的連結。
在《紀念日》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真菜」這個角色,真菜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女孩,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年代出生,她的媽媽是常常在媒體前做菜的知名料理研究師,雖然這麼會做菜,在媒體面前維持家庭和樂的形象,但真正的現實生活中,卻充滿婚姻和親子問題。讓我不由得想到日本食物被做出來時,常常有漂亮的顏色搭配,可是在漂亮的便當之中,真的是一個這麼完美的呈現嗎?這是我在窪美澄的小說中看到非常有趣的一個對比。
同樣的,一青妙在新書中提到,媽媽在她十一歲前為她做的便當是台式便當。台式便當我們都知道比較湯湯水水,不管怎樣做,蒸出來都是不好吃的,特別是青菜,有的青菜蒸出來就整個黃掉,無法避免,跟日本便當不同,日本便當因為都是冷的東西。所以一青妙在書中提到,回日本後的第一個文化衝擊,就是她帶著媽媽的台式便當到學校,引起了同學的側目。是不是可以請一青妙小姐談一下這個部分,因為在這部分也看到媽媽為了這個家庭,為了爸爸或孩子做了許多生活上的改變,談一下和媽媽之間的關係。
一青妙:我現在才知道台灣小學有營養午餐,雖然我的年代沒有,可是我回日本後第一次遇到就是營養午餐,當時吃到日本的營養午餐,覺得有點怪怪的,因為都不是手工做出來的,就像在便利商店賣的味道,我跟媽媽說我要帶我在台灣吃的便當到學校去,可是大家都看著我的便當,覺得便當很難看,雖然我自己不覺得,可是大家就用眼睛盯著我的便當,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慢慢的,我就想要帶和大家一樣的便當到學校。
媽媽於是就拚命的做出很好看的便當,用紅的番茄加上綠色的蔬菜,可是因為沒有加熱覺得飯硬硬的,所以,我就跟媽媽反映,於是她就幫我做「即使冷掉也可以吃的便當」,像是三明治,但我還是忘不了在台灣吃到的便當味道。
所以現在回到台灣,會去買台灣鐵路便當,很多人跟我說日本的鐵路便當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但是在台灣不同的地方,吃起來都是差不多的味道,其實,這就是我媽媽做出來的便當味道……便當代表我媽媽,也代表台灣,也代表媽媽對我的愛。
女性為結婚學做菜?
張維中:我在漥美澄的小說中讀到,因為做料理改變了一切,想請漥美澄談女人為家庭的奉獻,談一下她對這個部分的感覺,還有對於她所寫的、所看的日本社會,女人是不是能因為自己做菜開心而為自己做呢?
窪美澄:我覺得現在的日本社會,女性對自己的價值觀,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像剛剛提到,作品裡面,年長的世代沒有就職機會,可能家裡做生意,才有可能去上班或在家裡經營。其實我父母那一代,女性幾乎都是家庭主婦,做料理是為了家庭、小孩、先生,一心一意只有家人,對他們的愛有點太沉重,給他們這些飲食,反而會讓小孩覺得痛苦,雖然料理跟飲食對家人來說,是很強烈的愛的表現,但相反,也是束縛跟壓力。但我這個世代,很多女性會有自己的工作跟職場,要兼顧家庭就要做菜,丈夫可以協助,但可以協助的人其實很少。
張維中:一青妙觀察的日本社會有什麼特別的變化嗎?我發現日本女性為了結婚,會去料理教室上課?
一青妙:台灣沒有嗎?
張維中:台灣人都吃夜市(全場笑)。
一青妙:對,這就是台灣的優點,一出門就可以吃、可以買。
張維中:我看到日本很多人為了想要結婚,第一個要素必須要練就一身好廚藝,但很多人並不是很會做菜,所以會去上料理教室,當然也有喜歡料理而去上課的人,但有一部分的人是為了找到老公,是不是這樣?
一青妙:應該是吧,所以很多男人都被騙了。
張維中:日本的料理教室原本是針對女性的,後來也開放男性參加,但男性並非對料理有興趣,而是覺得那是一個可以認識女生的場合,實在很有趣。是否可請一青妙談談,自己印象深刻的菜色。此外,從小到現在,甚至在媽媽過世後,妳一直想要重現媽媽的味道,但到現在為止,還是無法還原的菜色?
一青妙:有兩個,第一個是因為我父親非常喜歡喝酒,所以母親做出來的菜大部分都是下酒菜。日本人喝酒時會吃的一種非常鹹的醃漬物,或醃漬的魷魚絲,還有一些就是只有喝酒的人才會吃到的東西。我從小就是一直在餐桌上看,我現在不會喝酒,但是可以邊吃麵包,邊吃醃漬物,對我來講,就像吃薯條一樣的感覺,那是我母親所做出來的味道,也是我小時候聞到的、印象深刻的。第二個是我媽媽做的蘿蔔糕特別好吃……我是發現母親留下的食譜之後,才知道要做一個蘿蔔糕不是那麼難,儘管如此,現在還沒有做出來的就是蘿蔔糕,因為做來做去,有時候覺得太硬、有時候太軟。
在日本很難買到在來米粉,所以我在台灣就會買在來米粉回去,我已經買了十多包,還是無法重現,在台灣如果有人可以教我,希望可以學到。
張維中:提到蘿蔔糕我感同身受,因在日本吃不到好吃的蘿蔔糕,中國超市有賣蘿蔔糕也都不好吃,整個味道都不對,所以我看一青妙寫蘿蔔糕就特別有感觸,這次回來要帶蘿蔔糕回去。對於周遭的日本朋友來說,用蘿蔔去做成的糕,感覺是無法想像的東西,沒想到吃到以後都感覺很驚訝,然後每個人都叫我做給他們吃。
一青妙:你會做嗎?
張維中:不會啊,這就像許多人覺得大阪人一定要會做大阪燒跟章魚燒一樣,碰到台灣人就覺得每個人都要會做蘿蔔糕。
漥美澄
日本受關注的新人小說家之一,二○○九年以作品〈水分〉進入文壇,收錄此作品的《不中用的我仰望天空》一書,於二○一○年榮獲日本《書的雜誌》年度十大好書第一名。
一青妙
父親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的長男顏惠民,母親是日本人。十一歲遷居日本。齒科大學畢業後,擔任牙醫師工作,同時兼顧以舞台劇、連續劇為主的演藝事業。
張維中
台北人,現居東京,任職傳媒業。大學時以長篇小說踏入文壇,迄今出版著作二十四部以上。小說與散文反映都會現況,內容多觸及家族議題、家庭再定義與組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