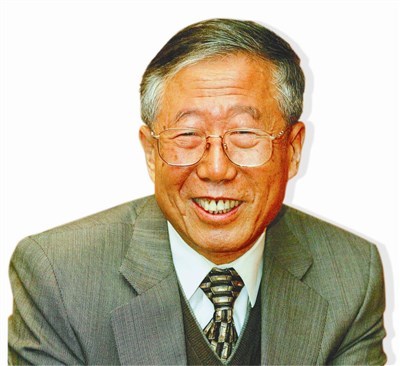 張作錦(聯合報顧問)
張作錦(聯合報顧問)
執筆人:張作錦
「九歌」《一○一年散文選》收錄了我的一篇小文〈斗室裡的「大觀園」〉,是悼念大陸「紅學家」周汝昌,並追懷他與胡適一段「忘年交」的往事。
文章無甚足觀,但故事的確動人。燕京大學西語系學生周汝昌寫了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被「名滿天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賞識,胡主動寫信給他,稱他「先生」,鼓勵他研究「紅學」。兩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面,胡就慨然借了三本紅學名著給周,其中一本還是當時世人未見的珍本書《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周汝昌由此成了俞平伯之後的大陸「紅學泰斗」。
百載的北京大學,像胡適這樣的人、這樣的事,似乎成群結隊而來,形成那一代的文風和世風。北大教授陳平原長年沉浸在北大的人文氛圍中,藉由對當時思想的素描以及後人的追憶,闡釋北大背後不朽的人文精神。
陳平原曾感嘆的說,現在北大教師很少有可述的故事了。事實上,不僅北大,包括兩岸三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在內,「故事」好像也愈來愈少了。這就難怪今人常覺有點寂寞。
當彼時也,大家尊重有真才實學的人。蔡元培讀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就請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學。胡適讀了沈從文的小說,請他到北大中文系教書。梁、沈均無「學歷」。
另一沒有學歷的學者錢穆,原在蘇州任中學教員,一九三○年燕京大學聘他任教,並把一座大樓的洋名「M樓」改稱「穆樓」。
華羅庚自十六歲自修數學,二十一歲寫學術論文,雖只是一個中學的事務員,清華大學卻延攬他到數學系任教。
一九二五年梁啟超到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任導師,向學校推薦陳寅恪,校長聞陳既無學位又無著作,頗有難色,梁生氣說:「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碩士,著作倒可算等身,但加起來不如陳先生數百字的價值。」
為人師表的人,要對自己的學問和人格有自信,才能使學生信服。辜鴻銘在北大上課,學生看他拖著長長的辮子而大笑。辜靜靜走上講台,慢條斯理的說: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裡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眾生肅然。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湯用彤在北大教書,主持中研院史語所的傅斯年請他兼一個辦事處的主任,送他一分津貼,湯退回說: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拿一分。
馬寅初曾任浙江大學和北京大學校長,因《新人口論》與毛澤東吵架而被批鬥。他說:「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也要出來應戰,絕不向以力服人者投降。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我想的是國家民族大事。」
今之學者喜談愛國,過去學人似乎「只練不說」。張伯苓在劉公島見中國水兵與英國水兵在體能和精神上的天壤之別,受極大刺激,所以辦了南開大學。
「九一八」事起,傅斯年知日本野心不可戢止,連夜邀集多位史學家趕撰《東北史》,提醒國人勿忘東北,勿忘國恥。
學校固然應有學養深厚的老師,也應有知書達禮的學生。朱光潛在校園散步,騎單車的學生經過他都會下車。
今天大陸上的大學,「一把手」是黨委書記,不是校長。台灣的大學以民主方式治校,校長的權力與責任有時是聊備一格。
大學請老師論學歷而非學力,且需本校、本系畢業的才行,大家競相「近親繁殖」。
而教授忙於「製作」論文在國際刊物發表,忙於申請研究獎助項目並「設法」報銷,不知還有多少時間用在學問和學生身上?
而學生呢?整夜上網,早晨的課沒有人上。穿短褲、拖鞋參加校慶會,校長在台上講話,學生在台下低頭玩手機。
不是校園「人文故事」少了,而是「人文」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