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喜母親墨竹。愈觀古今畫史墨竹,愈覺其墨竹,神采靈秀逼人,出類拔萃;愈繪墨竹,愈明其墨竹妙不可言處。迄今沉迷文學藝術數十餘載,人生體驗亦較深刻,讀其筆墨,更為其內涵、深度折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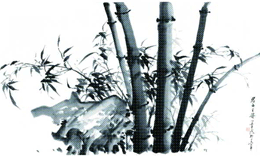
若言所繪忠實反映畫家性格、修養,母親所繪竹,不事小巧,滲入數數生死以之,出入大山大水的胸襟,凝之為竹,毫無嬌柔媚態,亦無歷代對女性畫家多所論定之「閨閣之氣」,如其行草「秀麗險峻」,則其墨竹氣魄雄偉剛勁,輝映古今,不讓鬚眉。
是否纖弱之身,僅得娟秀而已?是否品讀墨竹,皆需依循畫史、畫評?或有畫史,舌燦蓮花,此淋漓盡致,彼亦淋漓盡致,籠統交待,乏以細緻科學方法,客觀分析不同畫家異同之論。或有畫評名家,憑一己喜好暢言,即無筆墨經驗,亦可呼風喚雨。故僅依畫史、畫評所言,判別畫品,恐鑑賞未真。
繪畫非僅一紙、數筆而已,眼之所見,筆觸賦色等,實映照內心,內在涵養,自然流露。竹既為四君子之一,理想上是否能以君子之氣節繪竹,方得君子之格?凜然氣魄,如何養之?亦需畫外求畫?
母親生於戰亂,幼時喜擬花木蘭、梁紅玉、秋瑾等英雄氣節。其父言多讀詩書,胸中自有丘壑,故習畫之餘,亦廣涉獵詩、書、古琴,自勵奮發。如少時喜讀曹植《釋愁文》等,後困愁城,屢屢自解,欣然有方;陸機《演連珠》借喻委婉,處世道理豐富,又可認識大千世界;蘇軾《赤壁賦》既灑脫豁達,又有「天地之間,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莫取」等畢生受用之句。
涵泳詩書雖為修心,賦予畫藝深刻內涵,然透過繪竹,亦可修養心性。母親繪竹,心靈所寄,無非白居易《養竹記》所言,固、直、心空、節貞等竹之賢德,借以砥礪言行。
至若凜然之氣,如徐文長墨竹,如爆裂怒吼,欲襲其瀟灑者眾,然無其亦文亦武,滿腔抱負,為國翦除倭寇,終抑鬱不得志之剛烈,恐僅得皮毛。欲以怒氣畫竹,非外在似怒狀即成。若無內涵,身處豐厚,安居飽食,又無跋涉山水,登高望遠,品天地正氣,參古今之變之胸襟,不經風霜冰雪,如何養其氣魄?
從母親秉性正直耿介之性格來看,個人以為她實踐了文人畫的理想。真正的文人畫,應是出於內在修為與胸襟,並非形式是文人畫,寫意重於寫實,詩畫同律,即為文人畫。其所繪墨竹,君子之風,凜然之氣,胸襟氣魄,既靈秀超俗,又格局寬宏。不僅其四君子,水墨白描人物等如此,即使畫牡丹,喜氣年景,或其它用色濃豔之題材,亦不落凡俗,個人氣質,躍然紙上。
既欲專精於一,自古多言師古與師造化。揣摩古人者,可從母親臨文同倒垂竹可見一斑。偶與論竹,則吳鎮觀察自然,寫形極佳,非同無甚觀察,只能寫意者。板橋造型特異,側鋒寫葉應不宜學,然才氣縱橫,意境不凡。傅儒文人風格秀逸,葉數片耳,默然不語,積埋於心,內在豐富,而許多詩畫雙絕者,實以詩為主,畫則寫胸中意。
師造化者,母親厚實的寫生基礎,實為她出類拔萃之因。十餘年前父親來美,見所繪竹,似乎對我如此即繪,頗不以為然,提及母親往昔如何寫生、觀察生、嫩、老、斷、殘及風、雨、晴時不同姿態。於今母親所觀察竹,不下三千種。其師造化之寫生功夫,可謂正如元李衎之於其竹譜。
依個人繪竹經驗體會,總覺畫竹最難。創稿極難,而創竹稿尤難。別的題材,幾乎只要寫生,即可創稿。惟竹品類繁多,動靜變化複雜,古人雖於發竿出枝、織葉結疊,如偃月橫舟,魚尾飛燕等,已理出頭緒,但果真如彼法寫葉,卻如套公式,僵硬無趣。若面竹寫生,眼之所見,一枝一葉,老實寫來,所繪雖似竹,亦不得其妙。
母親所繪墨竹,除年少初繪,略為拘謹,然靈秀逼人。成熟作品,靈活奔放,瀟灑而不恣肆,造型變化豐富,不拘一格,無不創稿。葉、莖交織,似有法似無法,方覺得法,又為天外飛來一筆、一點破之。若必言法度,則可謂已臻隨心所欲不踰矩之境。然實已超越法度,渾然天成。或姿態蘊藉,婉約古雅,或飄逸出塵,閑靜恬澹,或穆然森森,如奇巖險峻,而各種風雨之姿,微風和煦,或颶風凌厲,神韻凜然。
母親為何寫竹?非不傾心清幽之蘭,玉骨冰心之梅,唯既生藝術世家,已有人畫,不得承許,唯有竹子,尚無人畫之,乃得畫竹。
其父曉以專一之理,如樹之主幹,分枝太多,無法茁長,然母親亦以縱列隊方式數列並行,長久堅持以往,長時投注,順應各種環境,遇風雨結冰,以鉛筆繪之,遇燈光不足,無法正觀色差,乃繪墨竹,六十餘年,始終如是。
母親寫竹,非詠竹而已。一九七三年出版國畫集收錄之〈幽竹〉,不就是她自己?而「頻顧多苔蘚,無計綰幽禽,豺狼在左右,風雨更相侵」非即一生艱難情況之寫照?
母親一生雖數經窮迫,然淬礪磨練不稍懈,心機震撼,靈機逼通,經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凝寫為竹,可謂標格韻致,澹漠超於艷冶濃麗之外。虛心誠心賞之,實古今畫壇不可多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