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貧困地區,有很多孩子中午沒東西吃,他們的身形十分矮小,掛在孩子臉上的兩朵「高原紅」,有的禁不住長期風吹日晒,還滲出血絲,看了令人心疼。這不是電影場景,也不是六十年前解放之初的景象,這是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大西北甘肅偏遠山區,一個個被世人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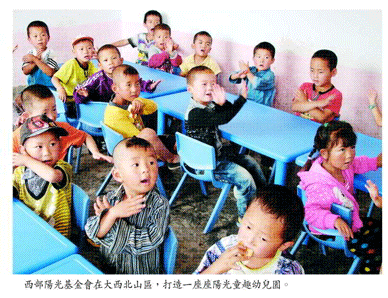 忘的農村。
忘的農村。
在中國大西北的深山,到處都是貧脊的梯田,飽經風霜的農民,臉上有道不盡的苦難,落後的山村中,更不時響起農村教育的悲歌。
這裡的世界,和台灣不同,和大陸繁榮的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灣城市,也不一樣。在外來者的眼裡,它是另一個國度,一個鳥不語、花不香、骨肉分離、甚至「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地方。
過去,山裡的明天,和昨天、今天,沒有什麼兩樣。長期被阻隔在外的村民,一直過著「自生自滅」的生活。
前往甘肅隴南地區的小山村,必須翻越一座又一座大山,映入眼簾的,不是天然的美景,而是望不盡被蹂躪的山頭。
這裡的人們,看不到「藍天」。山很高、動輒海拔二、三千米,感覺天空很近,然而距離天堂卻是那麼遙遠。
生活在大西北山區的農民,有著頑強、堅苦卓絕的生命力。為了生計,他們經常頂著高溫、冒著寒霜,有時還要忍受冰雪,長途跋涉到陡峭的梯田幹活,天天過著早出晚歸的日子。
山上的孩子,為了讀書識字,天還沒亮就得起床、晚上則要摸黑走山路。每天翻山越嶺、徒步三、四個小時,才能一圓上學的美夢。
然而,甘肅隴南的偏僻山區,普遍存在師資嚴重不足、教學品質低落以及學生營養不良等問題。很多代課老師都是農民兼任,他們不會說普通話,更不懂英語,卻是當地兒童的現代「孔夫子」。
在貧困地區,有很多孩子中午沒東西吃,他們的身形十分矮小,「童年」似乎特別長,「長」的有點不可思議。掛在孩子臉上的兩朵「高原紅」,有的禁不住長期風吹日晒,還滲出血絲,看了令人心疼。
這不是電影場景,也不是六十年前解放之初的景象,這是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大西北甘肅偏遠山區,一個個被世人遺忘的農村。
悲慘的世界
從甘肅省會蘭州到隴南地區的宕昌,「只有」五個小時車程,從宕昌縣城到好梯鄉,也不過兩個多小時的路途。但是,七、八個小時的「旅程」,卻從一個繁榮的國度,走進另一個「悲慘」的世界。
距離九寨溝和舟曲不遠的宕昌,是一個出產中藥材、核桃的窮地方,別說台灣人不熟悉,連一般大陸人,也很少聽過它的名字。從縣城到好梯鄉,必須翻越三座大山,其中,有不少狹窄的公路,至今還是黃泥地。晴天時,車子一過就是黃沙蔽日;下雨天,則是泥濘難行,而且完全沒有任何屏障物,一不小心,車子就會開下斷崖。
對膽小、患有懼高症的人來說,搭車到隴南深山,是一段驚險的旅程。可怕的程度,甚至超過坐雲霄飛車,不只心跳加速,手心和額頭,都會嚇得冒冷汗。
Google地圖找不到的宕昌縣好梯鄉,究竟有多偏僻?到底有多難走?二○一一年暑假,在大連大學就讀的王一奮,在山中當了一個月的代課老師,他在「支教日記」中,有不少生動的描述。
「狹窄的山路,只能容許一輛車通行,眼前一個彎,又一個彎。」「山的那邊,是一個又一個的彎,用蜿蜒、崎嶇來形容,唯恐小覷了這條山路。」「古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說法,應該不過如此。」
「轉過一個又一個彎,千辛萬苦抵達好梯鄉傅家庄小學,也就是山的那一邊。還沒有看到學校,淚水已經在眼眶打轉。」「當地沒有最崎嶇的路,只有更崎嶇的路。」「七十度的山坡,是我們家訪的必經之路,攀岩過程中,一不留神就會滾到山下。」
另一位前來支教的王長健,提起驚險的旅程,依然心有餘悸。他表示,山路另一邊是萬丈深淵,開車大叔一路上小心翼翼。不料,半路上,突然下起大雨,原本顛簸的山路,變得泥濘難行。
忽然間,眼前一處拐彎處,隊友所乘坐的車輛,因為剎車有問題,只差毫厘就掉進懸崖,大家都嚇出一身冷汗。還好,經驗豐富的司機大叔,在最後一刻,用方向盤化險為夷。
事實上,和三年前比起來,這裡的路況,已經明顯改善許多。之前,連條柏油路都沒有,村民對外交通,主要靠兩條腿、騎馬和摩托車。說起來,不免令人感傷,這裡的公路建設以及校舍重建,都是拜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帶來的自然災害所賜,不過,山中的建設,多是虛有其表、一種「假象」,根本禁不起大自然和時間的考驗。
位於半山腰的好梯鄉傅家庄小學,全校有學生五十三人,包括校長在內,只有三位老師,而且都是非專任的代課老師。校長李處林、老師杜文智、苟忠岐除了英文之外,幾乎什麼都教。
除了杜老師本身住在傅家庄之外,苟老師、李校長都來自外村,上下課,都要靠兩條腿走路。一般村民很少出遠門,即連學校的三位代課老師,也極少走出深山,頂多每年的農曆年前,會去一趟縣城採買年貨。
有五十多年歷史的傅家庄小學,二○○六年重建,周邊七個合作社的孩子,都到該校就讀。不過,這個偏遠的小山村,一直到二○○七年,村子才有電,二○○九年,才正式開通對外的公路。
如果不是這兩年政府大力推動「兩基」,也就是所謂的「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傅家庄小學的條件更差,而且差到令人難以想像。
過去,孩子只能幾個人共用一張桌子,讀書寫字都要分配時間,教室連個黑板、粉筆也沒有,不但老師教學吃力,學生學習也備感辛苦。村民簡直就是「化外之民」,農村基層教育無異於「放牛吃草」、「自生自滅」,令人不勝唏噓。
事實上,種田只能勉強溫飽,村民主要經濟來源,還是靠年輕人外出打工,一般都到新疆、陝西及山西,從事摘棉花、挖煤等勞力工作,留在村中的,則泰半是老人和小孩。公路通車以後,村民外出打工風氣愈來愈興盛,但是去年的平均年收入,仍然不足人民幣五百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