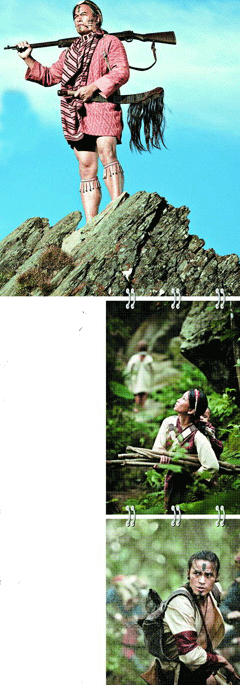
觀看《賽德克巴萊:太陽旗》的時候,我總會聯想到梅爾吉勃遜導演的電影《阿波卡獵逃》,故事背景是中美洲的原住民,不同部落之間以弓、矛、刀彼此征殺,武力獲勝的部落擄走失敗的部落人民,把他們當奴隸一樣販賣。當原住民族在原始森林裡互鬥時,渾然不覺歐洲白人已經駕駛大船,帶著更先進的武器,準備從海岸線入侵這塊「新大陸」了。
從史詩的角度去拍攝原住民電影,無可避免都會呈現此類「部落文明」跟「現代文明」接觸的題材。在《賽德克巴萊:太陽旗》中,原住民跟漢人好不容易和平相處,部落之間卻互相爭奪獵場,彼此殺來殺去。此時,日本人已帶著更先進的武器,入侵這塊島嶼了。
在現代文明強勢的「教育」下,弱勢的一方已逐漸放下直接獵殺的部落征戰,但是,當賽德克人決心「出草」(台灣原住民獵人頭習俗,與祭祖的儀式有關。)以生命反抗強勢民族,那麼,原住民如何安頓自己的身心,為自己的復仇找到一個好理由?
祖靈信仰文化
導演魏德聖選擇以「血祭祖靈」為切入點,呈現賽德克人在日本人的高壓、剝削式的統治下,原住民心中懷抱的信念是:「我不是在殺人,我是在血祭祖靈。」然後全力出征,砍下日本人的頭。
祖靈信仰是原住民的特有文化,每一位地上的子孫,都跟祖靈的國度有所連結。當莫那魯道決心以武力反擊日本人時,他在山涯邊獨舞歌唱,向祖靈宣告,向祖靈祈求力量。若是從漢人的文化去認識祖靈信仰,大概勉強可以用「緬懷祖先」、「慎終追遠」和「祭祖」的概念去理解。
看了電影《賽德克巴萊:太陽旗》之後,筆者當天晚上作了一個夢:我跟爸爸並肩坐在一台古代的馬車上,沒有馬,車子自己會動,我們彼此沒說話,只是微笑著欣賞路邊的風景,眼前盡是寬闊的米黃色道路和原野,遠方有一座高山。
夢醒後,那份平靜安逸的感覺還停留在我心裡,彷彿還跟爸爸並肩在同行。我想起電影裡,莫那魯道在湖畔獨處靜心時,跟父親亡靈一起吟唱,重新取得生命勇氣的情節。當我愈來愈清醒,突然間意識到,爸爸早已過世了,原來,這個夢是祖靈進入我潛意識的撫慰。透過這次經驗,我粗淺地體會到,跟祖靈的連結是怎麼一回事。
電影風格特色
導演魏德聖上一部作品——《海角七號》裡,每個角色都有憤怒的情緒,講話很衝,就連小女孩在教會彈鋼琴,都以快版的方式彈奏,讓唱聖歌的人差點喘不過氣來。只是,種種的憤怒最後都成就了歡笑,讓《海角七號》保有海邊小鎮輕鬆的風格。
同樣的,在《賽德克巴萊:太陽旗》裡,憤怒的情緒再度在全片蔓延。不同於《海角七號》裡的歡樂,這股發生在山林裡的憤怒漩渦,帶有沉重的敵意,那是不同部落之間的生死交會,也是不同民族之間的對抗。站在日本人面前,莫那魯道或許是英雄,站在其他部落面前,莫那魯道卻是殺人之仇的敵人。
個人認為,這種蘊藏著憤怒能量的電影風格,也跟魏導本身的生活狀態有關。魏導為了拍出心中理想的電影,必須四處籌資借錢,甚至把房子拿出來抵押貸款,然而,借來的錢都是要還的,萬一票房不佳,該怎麼辦?魏導長期受金錢壓力之苦,壓力會使得一個人處在憂愁煩躁的狀態,而魏導創作的電影,似乎就成為他宣洩壓力的出口,不論《海角七號》或《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幾乎每個角色都有他(她)暴躁發怒的理由,也許是原住民學生被日本老師欺負,也許是父親聽不進兒子的建議。這些情緒,讓觀眾也跟著進入沉重的氛圍中。
「憤怒」是魏德聖導演現階段作品的特色,期待魏導能有更順遂的經濟生活,轉化壓力,投注其他能量在電影中,呈現不同風貌給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