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幕色低垂。接獲客堂知客急電,告知有位老菩薩遠從大陸來,一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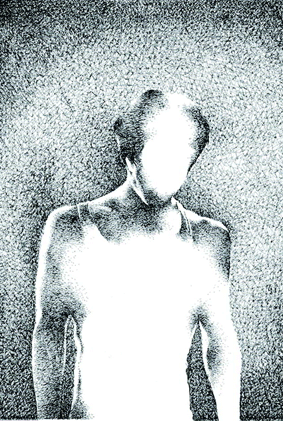 要見我一面。天色已暗,窗外微雨,我又急著要去上課,心裡十分猶豫。但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仍快步拐回寮房,順手拿了些結緣品,便信步往客堂走去。
要見我一面。天色已暗,窗外微雨,我又急著要去上課,心裡十分猶豫。但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仍快步拐回寮房,順手拿了些結緣品,便信步往客堂走去。
經過不二門前廣場,有位老人家在一對中年夫婦的陪伴下,瞪大著眼,正費力地張望著過往的出家眾。我趨前致意,確定自己是她要尋找的人後,便引領三人進入客堂。老人家面露靦腆,但不顧風塵僕僕的疲憊,笑咪咪地自我介紹起來。我聆聽著,喚起了對她的記憶……
三年前,我任執事知客師,引領一團大陸客巡山,就在行程快圓滿時,發現有位老人家滿臉落寞,一副若有所思,於是趨前關心,沒料她竟淚眼婆娑地對我傾述心中苦楚……
老菩薩是浙江浦江人,父親朱劍農是位將軍,一九四九年隨國民軍隊來台後,父女再也沒見過面;盼了近半個世紀,首度來台卻是來奔喪的,多年的期盼竟成空。所幸,竟然有短短一個半小時的參訪,讓她隨緣聽聞正法、認識人間佛教。在訪團行程圓滿前,老人家感動地對我說:「師父,謝謝您!您的一席話,我現在變成佛教徒了!」
老菩薩肯定的回應,鼓勵了我想再多「給」的動力,帶著他快步走向客堂,迅速地迎請出一尊磁製的佛陀坐像,夾帶幾本簡體版《佛教小叢書》,說明代表常住致贈之意。她垂皺的臉龐堆滿了笑意,接下致贈的禮物,並堅持要與我合照後!臨行前,依稀記得他說著:「我要做個佛堂,好好地供奉著,早晚稱念佛號!」
「師父,我給您帶來佛堂的相片,和當年跟您的合照!」
「師父,您瞧,我可是虔誠地供奉著佛像,並早晚上香、稱念佛號!」
「師父!您瞧,當年您給我裝佛像用的佛光袋,我也沒捨得扔。您仔細看看,就在佛桌旁的一角,我還同時供著呢!」
我連忙接下他遞過來那三張護貝、 泛黃的相片,心中湧起莫名的感動。老菩薩抖著音聲繼續述說:
「師父,我以為沒機會再見面了!因為這趟來台灣,訪團集體行動,是萬萬不能離隊單獨行動的。但行程到達中部,我就央求團長給我一些時間,便偷偷離隊,打了通電話給台中的弟弟,要他無論如何一定要載我跑一趟佛光山。師父,您看!我帶來了相片,就是要讓您知道我設了佛堂,我在念佛!」話才一溜出口,只見他又喃喃自語地說著:「菩薩保佑,讓我有幸告訴您這件事情!」
「師父,『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這九個字我可把它當傳家寶,力行在生活中的!」
見他不遠千里而來,只為了告訴我他落實佛法,這種感動與興奮是難以言喻的。不到一刻鐘的會面,只見他心滿意足地說:「師父,天晚了!我是脫隊而來的,得趕快歸隊!」我建議他在不二門前遙拜,聊表心意。話一出口,見他老人家二話不說,一股腦兒,奮不顧身地五體投地猛磕響頭。肥胖的身軀在微雨中,起身、俯地,膜拜再三。
課後,微雨下,頂著夜色回到寮房,仔細端詳老菩薩為我不遠千里所帶來的禮物:一張典型的鄉村佛堂相片,簡陋得可愛;板凳、圓桌、冰箱、電風扇,外加那張用長木條架起來的佛桌,佛陀坐像就擺置在福祿財神下的正中央;三張微黃的相片、用透明材質所製的七佛塔(可能是特意請購帶來台灣的),全塞在塑膠袋內,一股腦兒都堆擠到我的跟前。
心感當天行程匆促,有失圓滿。於是寫了一份信致意,附上簡體版《佛光小叢書》數本、 心定和尚的《大懺悔文》CD、《金剛經》、手鐲念珠一串,以及各式大小不同造型的中國結、佛卡。並註明「請轉贈夫人、公子,或鄰近親朋好友,共結法緣」。
個把月後,我驚訝地收到浙江省浦江縣的掛號信,還是用電腦排版打字的呢!除了洋洋灑灑的信函外,竟還附帶了朱老居士的一張全家福相片。細讀來函,我確定佛法的種子,已在對岸的人家中,深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