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富士山的第二天,很幸運地,我們看到了煙火祭。
下午四點半,我們騎著民宿的自行車,沿著河口湖繞行,想從不同角度看富士山。我們以悠緩的速度前行,不時在幾個定點停下來看富士山,看雲靄一點點地退去,富士山像個莊嚴卻又親切的修行者,從湖的那一端朗朗映現。似遠又近,守護般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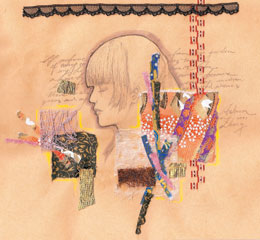
繞回民宿的路上,河口湖的南方較為幽靜的露營區,有人已經搭起帳篷,在棚外張羅著晚餐,烤肉的香味順著風勢飄至路旁。漸漸地,我發現入山的車輛多了,警察進行交通管制,許多年輕男女穿著浴衣從河口橋那端走來。吃食的小攤小舖不知何時已整齊地排好,小販忙碌地張羅著。整個河口小鎮隱隱籠罩在節慶前的歡鬧氛圍中。即便如此,我仍去超市買了點食材,回到民宿做了簡單的晚餐。因為吃素的關係,也因為想多吃幾樣熱騰騰的鮮美青菜,而這兩者在日本餐廳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當然,也是因為我喜歡在旅行途中不時來點家常味道。
和前幾晚不同,民宿的廚房空了不少,工作人員說,大夥都出門了,準備揀個好位置看煙火。由於廚房鄰著一條街,邊下廚還可以聽見前往河口湖的人群嬉鬧聊笑的聲音。
快速地清炒兩盤菜拿到用餐區,發現SY已和鄰座的西方人聊了起來。問他是否等會要一起去看煙火?他說不看了,可能要回幾封信,做點工作。他來自倫敦--是個自行創業的電腦軟體設計者,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一同旅行日本三周,他們上周已經在東京看過煙火了。
快吃完時,聽到外頭陣陣巨大的聲響。煙火開始了。我們忙不迭地收拾碗盤,準備出門。在櫃台看到了工程師的兩個女兒,他們正上網收信,專注地凝視著電腦螢幕。外頭聲響大作,天邊有光,如火燒黑夜,彷彿異景。連民宿的工作人員都跑出門外,看煙火去了。但這兩個英國來的金髮少女無動於衷,在這樣聲光震震的夜晚,坐在民宿裡,連同待在用餐區工作的老爸,任由螢幕藍光清晰他們的眼,照亮他們的臉。
彷彿異景。
我們不僅看煙火,也看人。多麼喜歡他們賞煙火的那般情致,女孩們穿著各種顏色的浴衣,將長髮高高梳起,並在髮上別了簪,小巧晶亮的點綴,在夏日夜晚裡飛成了流螢點點。一群女孩走來,浴衣上盡是夏日風景:綠竹、朝顏、煙火和所有足以歌頌青春的粉紅嫩黃淡紫。她們邊走邊聊,邊吃著棉花糖或冰淇淋,另一手則勤快地搧動著小圓扇或摺扇。扇面又是另一處風景。
腳下人字拖也搭配著浴衣和團扇的色調。幾乎所有看到的女孩都不忘替腳趾甲上色,全是青春正好的顏色。
幾乎全是這樣的女孩子,她們費心打扮,從每一個細節都看出她們的用心,但每個細節卻又盡可能貼近於某種自然的節奏,不張揚,不繁複,不喧嘩,不做作。她們將夏日穿在身上,讓自己成為湖光山色之外的另一處自然。她們成了夏夜裡的流動風景,成為晚風,成為流螢,成就繁繁點點的美。
走在一群穿著浴衣的女孩子的後頭,挨著賞煙火、逛夜市的人群慢慢地向前走,感覺晚風送來了女孩身上沐浴精和洗髮乳的香味,以及燒烤海鮮肉類的味道,這種氛圍告訴我,煙火開始了,節慶開始了。
大約十來分鐘就施放一組的煙火。煙火燦燦,點亮了天空,以不同形狀從黑暗的帷幕中一絲一毫地長出來,有點,有線,有花絮,像極了我們平常能喊出名字的日間物,如花,如琉璃,如毛線球兒,如貓咪的爪痕,如生命的開端。如宇宙的源起。但定睛一看,又覺得那樣的東西並不屬於世間,太璀璨,太神祕,太超然,太無懈可擊,美得令人屏息卻又短得不如一聲嘆息。
從煙火發射到爆炸開來,許多相應的名詞和形容詞同樣在我腦海中一朵一朵迸現,我還來不及確認那些詞彙,煙火和文字同時消失,留下灰濛濛的天,留下尚未理出頭緒的我。
但相較於煙火從天空爆炸開來時的火樹銀花,我更喜歡煙火全然消失前所留下的淡淡軌跡,那接近尾聲的殘跡。比起盛開的煙火,我總覺得那樣的殘痕更令人心安,更值得依靠,更久駐人心。是我太悲觀嗎?我一向害怕太美好的物事,依照過去經驗,太美好的事情背後總攜帶著危險訊息:短暫,脆弱,易碎品。好物不堅牢。正因過度依賴著美好的物事,所以當人去樓空,一室空寂才更難忍。
記得小時候最喜歡表妹來家裡玩,雖然不記得玩了甚麼,想來不過是扮家家酒、角色扮演;但玩起來也特別投入,希望時間永遠停在這一刻。因此每次表妹要隨舅舅離開我家,我都故作鎮定,面無表情地說再見,其實是躲回房間大哭,久久不能平息。某次媽媽撞進房間,看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好笑地說,下禮拜他們又要來了,有甚麼好哭的。
但我就是不喜歡分離的感覺,不喜歡美好時光總有結束的時候。某次看綜藝電視主持人在節目尾聲說,啊哈,美好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咻」一下子就過了,當時才小學四年級的我聽到這句話,竟如五雷轟頂,原來這就是答案啊,眼淚一下子掉了下來。
後來發現,主持人每周都說同樣的話,用同樣笑容和聲調說,美好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咻」一下子就過了。
於是我開始避開最完美的時刻,當表妹、妹妹和我玩興正濃時,我會趁著他們不注意時悄悄離開,當表妹要離開時,再突然出現,故作鎮定,面無表情地揮揮手,再見,再見。漸漸地,我竟然希望他們連出現都不要出現,這樣再也不會分離,希望美好的時光永遠不會到來,既沒有開始,也無所謂結束,再也不用說,再見。
是啊,沒有開始,就無所謂結束。
因為煙火,這群人才坐在這裡,從東京、不知名的小鎮來到這裡,穿上有著夏日氣息的浴衣及涼衫,來到河口湖,等著夜的來臨,一邊喝啤酒、吃燒烤又一邊看著煙火從湖的那一側被用力彈出,像精子奮力游進黑暗的子宮,而後倏忽爆炸開來,成為許多可命名或不可名狀的種種物事。煙火施放期間,有人驚呼,有人鼓掌,有的人架起專業相機,試圖捕捉美的軌跡。有的人則靜靜地望著盛開又凋零的煙火,在天邊生了又滅,滅了又生。
大多數的人;尤其是穿著夏日浴衣的青春少年女子們則是走走停停,戴上不太搭調的螢光蝴蝶結髮飾,手裡甩著各式各樣的螢光棒,嬉鬧著,聊笑著,吃著章魚燒或冰淇淋,聊著學校裡種種有趣、無聊、不值得一記的瑣碎事件。看起來他們不甚在意煙火,煙火充其量只是大夥一塊夜裡嬉遊、逛街、吃吃喝喝的理由,煙火只是舞台,正好替他們鼓噪的青春、喧囂的身體提供了背景,因此即便煙火再美、炮聲再大,他們連頭都不抬一下,仍舊膩在與友伴構築的小世界裡。他們用廉價的言語照亮彼此的五官,用廉價的螢光棒照亮了彼此的言語。他們的眼神亮了,與煙火無關。他們浴衣上的山水樓閣亮了,與煙火無關。夜裡,他們身體裡蟄伏的煙火苗將從幽深的一處被點亮、彈出,進入另一座身體的廣袤天空,燦燦,燃燃,與煙火無關。
彷彿異景。
即便那樣不可思議的美的乍現及殞落,可能更接近於所謂的啟示,某種真理的示現:美得那樣令人屏息,令人心碎,令人流淚,卻又如此短暫,不可恃,不可留,不可言喻。如同我們一向熟知的古老智慧,如同我們早已聽慣了的溫軟歌謠。好物不堅牢。
抬頭看見的,既是煙火,更不僅是煙火。是煙火,又與煙火無關。
最後一發的煙火並沒有如預期那樣特別花俏、壯麗,只是如前。好在只是如前。人群開始散了,仍舊是那樣笑鬧著。成排的攤販前明顯空了許多,不像先前大排長龍,然而,小販仍勤快地製作一個又一個食物:烤魷魚、炒麵、棉花糖還有甜膩膩的巧克力香蕉,同時大聲吆喝,吸引人群來買,不過無法阻止群眾紛紛散開,人們收起了塑膠布軟墊、野餐籃、專業相機,牽起家人的手,成群地往旅館區和停車場的方向移動。
然而,小販對人去樓空的場景視而不見,對煙火的結束視而不見,對於節慶的終止視而不見,幾乎沒有任何人在排隊,他們仍勤奮地製作著一個又一個新鮮的吃食,一一堆放於展示台上,彷彿後方還有許多人在排隊,等著一個又一個熱騰騰的食物。
彷彿異景。
煙火結束了,人群散去了,他們仍對著逐漸淒清、空索的街大聲吆喝,像著魔似地拚命做著灑滿糖粉或裹著油膏的鮮美食物,一個又一個地排列開來。一個比一個更令人垂涎的鮮美食物就這樣被不停地製作出來,晾在風中,擺放在已然擁擠不堪的食物台上。
突然之間,我好像可以瞭解他們的感受。
彷彿再度回到那天,國小四年級的我坐在電視機前,看著主持人在節目的尾聲,堆滿笑容對我說,啊哈,美好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咻」一下子就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