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接近正午,天空卻一派陰霾沉鬱……但久久未見飄雨。我們默然地序列妥當,即將目送一場肅穆的儀式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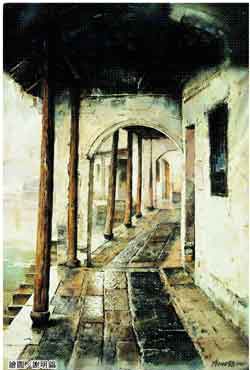
三名衣著繁瑣的道士誦經領頭,家屬在後方渾渾噩噩地追隨著,彷彿童話《魔笛》裡,那被笛聲催眠勾引的村民。行屍走肉一般。我的思緒極其清晰:三日前才剛過完闔家團圓的中秋節。俟一行人步至焚化爐前,道士平淡地囑咐著:
「待會火一起,看你們與死者是甚麼關係,就大聲喊他『火來了,記得跑開。』」
我想起祖父一年四季皆只身穿薄薄的汗衫短褲而已。他耐不住熱!
「阿公!火著了,緊閃開喔。」啊,我想起祖父是極怕熱的!
偌大焚化爐的三個爐口接踵運作著,閘門開啟閉闔,片刻不消停頓———後頭還有好幾具大體在排隊等候火化。聽說今天是好日子!難怪,整個火葬場裡人滿為患,一家比一家哭得大聲,一家比一家吼得淒厲。我卻覺得,人世間再沒有比這更加荒謬的反差———如何定義「好」日子?對於即將要忍痛送走至親最後一程的家屬來說,哪還會有搆得上「好」字的那天?
很快地,只需要半小時的光景,我意識到祖父終將捨棄一身舊皮囊,前往未知的國度去赴一趟沒有歸期的旅行。紀弦先生的〈火葬〉一詩,在我的腦海中娓娓浮現。
如一張寫滿了的信箋
躺在一隻牛皮紙的信封裡
人們把他釘入一具薄皮棺材
復如一封信的投入郵筒
人們把他塞進火葬場的爐門
酖酖總之,像一封信
貼了郵票
蓋了郵戳
寄到很遠很遠的國度去了
濃煙自筆直的煙囪冉冉飄升。那是祖父的單程機票。
高齡九十歲的祖父,身子骨其實仍硬朗得很,每天跑進跑出行動自如;唯獨腦筋退化地明顯,時常失憶迷糊。三個星期以前,祖父不慎跌倒磕撞到頭部,當下無人覺察,祖父也未喊痛,自行回了房間躺下歇息。直到傍晚母親喚他用餐,竟發現祖父陷入昏迷已不省人事,趕緊叫救護車送醫急救。
當時,我們業已規畫好了烤肉的出遊行程。
下了班,我趕去醫院探望祖父。加護病房有著嚴格的探病規定,我們直如探監般,在短得可憐的開放時限內,一點一滴榨出每個人所被允許的配給份額。寥寥數十分鐘,眼前呈現的卻是一場生與死的無聲拔河。祖父靜靜地躺在病床,鼻端插著呼吸器,手臂上延伸出數條透明纖細的塑膠管,彷彿才自體內生就;剛開完刀取出一部分凝結在腦中的血塊,頭顱頂端有道長長的縫線,令人怵目驚心。
「都一大把年紀了,還要受這種折騰!」母親不捨地道。
看著祖父孱瘦的身子動也不動,我輕緩地摩挲著他的手、他的身體、他的白髮……他一如童稚般安詳的睡臉,溫柔地細聲呼喚。祖父想必正做著好夢。他終究不願甦醒。
房間裡擺置著數十張病床,幾乎每張床前都圍著一臉哀淒、悲痛的家屬。他們的親人或意外、或疾病、或者生命已經走到了一個不堪折騰的地步,病患們正以自身註解著人世間最難讀通的鉅著,死亡。我又望向祖父:我未曾有過心理準備,有朝一日,我竟要從他的苦厄中研讀這門艱澀的課題。
所謂死別,好比你和他走在一條無法調頭的單行道上———你們徐徐地邁步向前,之間卻始終保持著一段固定的距離,沒有任何方法能夠縮小、接近。隨著時間拉長,你發現自己的步履愈走愈穩健,他卻是愈走愈顢頇。終於,他來到了終點線前,沒有絲毫遲疑停頓,一閃身便跨進了縹緲渾沌的另一場馬拉松。你明明還有很多話來不及傾訴,怎知一回頭,後面又有熟識的親人跟上了……
或許,龍應台先生看得要比我更透徹些: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母子女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目送》)
在小路轉彎的地方,不知道祖父會否回過頭來,笑著揮手要我不必追。
祖父夢寐後便沒有再醒來。尚未趕得及迎來中秋,祖父便因器官衰竭翩然離開,沒有一絲苦痛掙扎。我們從醫院直接驅車前往殯儀館,一路上不斷地呼喊著他,要他跟上。
這一次,他再也沒能用微笑回答。
我們就在殯儀館度過那年中秋 ———沒有喜慶的月餅柚子,只有哀戚的素果三牲;沒有歡愉的煙火烤肉,只有寂寥的紙錢香燭。象徵喜喪的紅色燈籠掛滿靈堂,好似墜落人間的月亮……而昏黃的月色又像極了高掛在天上的燈籠。只不過,天上的盈月揭示著闔家團聚,地上的燈籠卻透露出此生永別。
待火化完畢,道士將祖父焚燒後的遺骨取出,置放在鐵盤中。他擎著杵,恭敬隆重地把骨骸搗磨成灰———我瞧見在那頭蓋骨上有一道明顯的裂縫:是開過刀的痕跡,也是橫←在親人心頭一道永難弭平的傷痕。我們一人一鏟,將骨灰鏟進冰冷醜陋的罈子中,親手送祖父最後一程。
將祖父送抵最終歇腳的靈骨塔,我們結束了一趟莫可奈何的旅程。骨灰罈被鎖進了方整制式的櫃子裡,那一格格的寸室、一張張遺照都是最難解的生死書。步出塔外,煦日從雲層中探出一縷光來,照在父親蓄滿未理的鬍渣上,竟反射出點點銀漾。原來,歲月業已在父親身上烙下造訪過的痕跡。
如果我只能目送著父親的身影漸行漸遠,我必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記得隨時開口大聲喊他。
我一直都會在後頭跟著。請你要多留意腳下路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