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有些勉強,還是和朋友來到慈峰的發哥山莊。我們晚上九點自台北出發,在埔里稍做一些採買之後,約凌晨一點左右抵達。主人發哥已經睡過一覺起來迎接我們,並計畫往後數天要如何拍照。我已經是熟客了,也算是半個主人,一切打理都是自便。然而朋友初次來到山莊,又一心想要攝影野鳥,雖然是一起作客,心情顯然和我不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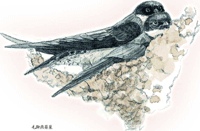
山莊其實是個果園農場,主要作物是甜柿。已經經營了三年,甜柿生長並不如預期般順利,大約有一半的砧木必須重新種植,加上發哥半途轉業,獨力開發經營約一甲多的山坡地,體力、經驗和年齡都是很現實的問題。所幸,隔鄰也是種柿子的徐大哥經常奧援,發哥山莊的甜柿仍然欣欣向榮,在中海拔山區裡吐著鮮嫩的綠芽。

慈峰附近也有不少果園、茶園,其中以徐大哥和發哥的果園最受爭議,因為他們從不除草,任由雜草荒天蔓地自由生長。徐大哥甚至替雜草施肥助長。
「雜草不但不會影響作物,根系還會固土保肥、也可以當作綠肥,改善土質。」徐大哥說:「植食性的害蟲有了雜草,就不會啃食作物。」保留了雜草省去除草劑和農藥的成本,還可以讓果樹在比較自然的環境下生長。農人不除草;天下米糧少,雜草叢生的果園,成為本區莊稼的笑柄。
一早起來,走在果園裡,遍地都是細蝶的幼蟲。這種外型可怖的小蟲,原本以有毒的蕁 科植物為食草,不過發生在果園裡,密密麻麻爬滿各種雜草,似乎有見青就吃的好胃口。牠們在自然界中務盡了「除草」的角色,於果樹反而秋毫不犯。走著,無意間驚起了幾隻竹雞自腳下的草叢中飛起。原來,竹雞在樹林裡的樹枝上過夜,在果園的雜草叢裡築巢。大約十點左右,山谷中氣溫升高,不常見的林雕在果園上空低飛,慢慢盤旋高昇。遠處山林裡還聽到了鷹鵑的叫聲,成群的毛腳燕更飛進附近工寮裡築巢。
發哥不善於料理,冰箱裡都是醃製的,可以久存的食物。每天總是吃一些方便的、回鍋的,又黑又鹹的滷味。這種吃法顯然對身體不好,因為吃不慣他的食物,每次來山莊都是由我掌廚,我建議他在山莊附近種一些蔬菜,或是保留一些野菜。這一次,我發現果園裡除了有野生薺菜和刺蔥之外,還有半野生的馬鈴薯和蘿蔔,以及龍鬚菜和紅菜。這幾天,我們的菜單中就有蘿蔔的嫩葉和龍鬚菜的嫩芽,涼拌馬鈴薯和肉片炒蘿蔔絲。這樣的吃法,對我而言直可說是山珍美饌了。
適逢周末,有三、五位發哥的友人從都市前來山中度假。山裡夜晚的聚會有好酒、好肉、好心情和好話題。餐後,朋友放映野鳥幻燈片秀,敘說他的攝影歷程和理念。一直到月臨西山才各自回房休息。
我們一直待到不得不離開的終極期限,才悻悻的驅車北返。發哥有些落寞,我們確實也十分不捨。我羡慕他擁有一塊什麼都長得出來的土地,有了務實落腳的根據。他則羡慕我沒有包袱可以到處為家。
亨利梭羅在華爾騰湖隱居寫作,不忘了嘲弄那些「不幸的人,生來就繼承一片土地和房產」,每天背著穀倉廢寢忘食的工作謀取經濟,然後再花錢去換取娛樂。百年來,經濟和休閒成為現代人生活的重心,似乎已經無可回天。如何以自然的方法取得經濟生活?要怎麼生活才能獲致休閒?什麼樣的休閒才能順應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