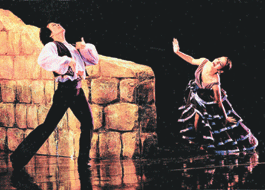
2000年陳偉誠與吳素君,詮釋蔡瑞月代表作「牢獄與玫瑰」。郭東泰攝
一九八五年,蘭陵劇坊跟政府申請經費,可說是台灣劇場史上,頭一遭有正式的官方經費,來支持劇場演員肢體培訓的活動。當時蘭陵與準備自美國返台的陳偉誠合作,而在美國師從世界戲劇大師Grotowski學習的陳偉誠,則帶回來完整地肢體律動訓練,轟動一時,後來「肢體律動」也漸漸成為健康生活的風潮。
陳偉誠表示肢體律動的核心並不只是在動作,更重要的是內心感受;如果能夠良好的連結律動來開放思想,或相對將思慮帶入律動去感受,那樣的肢體訓練才是成功的。
一切都是關於「人」
教學相長豐富經驗
「那我正好遇到一個老師(Grotowski),在我學習劇場的過程中,他使我很快地就了解到,一切都是『關於人』。的確我們是在做一個事業或志業,然而終究,無論我們的身分是什麼,與一切息息相關的還是在人與人之間,我們所成就的身分就是在推動這個時空可以去帶動的關連性。所有人的問題能有所解決,那很多事情也就得到解決了。」
這次的教學經驗,在陳偉誠回到美國繼續擔任大師的助理之後,有所發酵;陳偉誠認為,當然在當年返台之前,跟隨老師的時間也有一陣子,在工作上也體認到許多老師所說「一切都是關於人」;而讓陳偉誠回到美國繼續工作時受到的震撼是,「原來這就是所謂教學相長!」當學生的時候,以為自己吸收、了解的觀感,等自己也成為老師的角色之後,才明白還有更深的意涵可以去解讀。
傳承是自然而然
發生的事情
陳偉誠自己對於教學生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太刻意,他認為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很自然就會發生的。陳偉誠表示,在收學生的時候並不是特別考慮了要怎麼讓學生承襲這些技術或精神,一開始總是很單純地,有人願意學,那他也樂意教。
「我想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說後來就會比較去思考希望學生能學會或領會什麼,然後才會去想說要怎麼去傳承的問題。總是都會希望下一代可以透過我們的經驗,少繞一些彎子,能比較順暢地去達成目標。」陳偉誠如是說。
陳偉誠指出,像劇場的部分,這是一個創作的東西,而且完全驗證Grotowski所言,這樣的工作總是不停地在面對關於「人與人」、「人與我」、「我與我」之間,想把這個學好,就是要懂得處理這些關連性,而且要能懂得如何面對自己,與自己建立良好的溝通。那在這個反覆的過程當中,才能把創作不斷地製造創新。
嚴格自律 開拓視野
健康身心靈
談到這是不是跟宗教的意旨有些相仿?陳偉誠認為,雖然律動並不是冥想,也不含有傳教的目的,本質上則可以說是相通。良好的肢體律動之所以能打造健康身、心、靈,正是因為透過訓練,在動作間的快慢調合,其實都蘊含了很多能量,不僅僅如此,精神和身體的協調也是在進行同樣的訓練;這也是為什麼從事劇場工作,需要讓演員進行相關培訓的原因之一。
身兼「動見体劇團」藝術總監、編導、演員、舞者的符宏征說,陳偉誠的訓練其實滿嚴格的,尤其對時間觀念的規定非常絕對,遲到的人就不能進場上課,遲到三次就等同曠課三次,然後就可以不用再來了!
這可能還算是比較基本的,其他的部分就更是有所要求,能跨越途中那些困難,然後真的感受到後來身心平衡、自在的人,實在有限,以現在自己當老師來看,可以說能體會陳偉誠的用心。
成功的不二法門
思想結合行動
「不過我自己教學就比較輕鬆一點。雖然我是挺得過,但是我的個性會比較想讓學生去慢慢吸收,每次一點一點這樣去加總。」符宏征教學的方式,顯然也加入了自己的想法。
陳偉誠表示,這就跟他也不會完全去拷貝大師的教學方法一樣,尤其像他是跟一個歐洲人學習,就更能深刻感受到,不只是個性上的差異,在文化上的差異更是一個自己在教學的時候,必須去重視的問題,所以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直接拷貝老師的做法。
「思想和行動的結合」可以說就是肢體訓練的體現,陳偉誠指出,放大一點來說,做任何事情也都是如此;因此本質上很多世事都是相通的,這還必須看個人怎麼去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