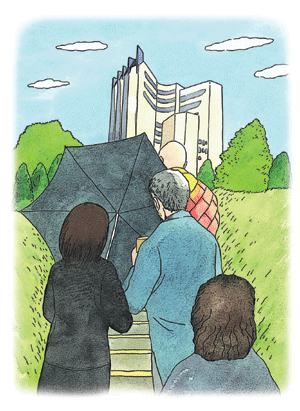 我從凱迪拉克的車窗往外望,晴空萬里,幾抹白雲悠然浮動,這是我第一次坐凱迪拉克,第一次行走中二高。車子從水里、集集的交流處下了匝道,眼前出現了南投鄉間常見孤挺的檳榔樹和疏落的椰子樹。嫁到草屯多年,我鮮少踏出婆家之外的鄉鎮,我像個過路客一樣,心不在焉的看著窗外的景色一幕幕倒帶般轉過。
我從凱迪拉克的車窗往外望,晴空萬里,幾抹白雲悠然浮動,這是我第一次坐凱迪拉克,第一次行走中二高。車子從水里、集集的交流處下了匝道,眼前出現了南投鄉間常見孤挺的檳榔樹和疏落的椰子樹。嫁到草屯多年,我鮮少踏出婆家之外的鄉鎮,我像個過路客一樣,心不在焉的看著窗外的景色一幕幕倒帶般轉過。
寬大的凱迪拉克裡,我和哥哥侷促的坐在一隅,車身正中央安放著母親莊嚴的黑檀靈柩,母親一定也會選擇坐凱迪拉克,風風光光的走完最後一程吧。我看看母親的靈柩,再轉頭看看身旁的哥哥,他疲憊的臉上已長出參差的鬍髭,就像田間一片荒蕪的亂草。哥哥雙眼微閉,一手拄在窗口,一手緊緊護著一支白幡。
車子經過了不知名的鄉鎮,開始上坡路,窗外的風景愈來愈青翠,已經來過好幾次的哥哥忽然出聲說,就快到了。中部著名的水里火葬場竟隱身在這麼一處風景秀麗的山丘上。
清晨七點左右,火葬場已有更早到的喪家,幾口火化爐俱以上千度的熊熊烈火輪番吞噬一具具棺柩。就在爐口封起來時,天人永隔的最後一個信物也就蕩然,有喪家呼叫著,「某某,快跑。」有的喪家請來的女子樂隊,則熱鬧的吹奏起流行歌曲,好似總要有點送別的儀式才能傳達不捨的心情,但卻又不知如何才好,各家就在火化爐前忙亂的表達情緒。
母親的靈柩被送入火爐時,原本鎮靜的親族,突然騷動起來,我聽到先是阿姨號啕大哭,再是表妹低泣:「阿姨,快跑!」跟著全體亂了起來,各自喊著「快跑」,我看到母親被推入熊熊的火中,母親走完了此生的最後一程,能否再浴火重生了?我望著走在前頭的法師背影,想著,如果生命果真有輪迴,那麼母親此生因何而來,因何而去?是為了賦與我們生命嗎?是為了成就我們嗎?在母親走完了人生路,我彷彿還對母親生命裡的許多事感到陌生。
我緩緩走回家人搭乘的遊覽車,經過火化爐的背後山坡地,被黑色的濃煙所震懾,那麼,母親的身體也化為煙霧中的一股,乘風而去吧。車上,叔叔正興味盎然的講著母親和父親的戀愛經過,都是些我從來沒聽過的事。我到底知道母親多少啊?我躺在遊覽車後座,對著車窗外的風景發呆。
母親剛過世,她的一位閨中好友,打電話給我,她說打了幾天電話,母親房裡的電話都沒人接,我告訴她,母親已往生,已罹癌多時的她在電話那頭繼續關切,「你知道你媽媽有沒有去燙頭髮?」我回說,已很少出門的母親在過世之前,剛去燙頭髮,回家後還興沖沖的告訴我:「頭髮燙一燙,比較像個人樣。」母親過世後,我幫她淨身,梳著那一頭新燙的髮絲,不免感歎母親一定沒料到自己的生命就這麼匆忙結束。我跟母親的好友說,母親去燙了頭髮,她欣慰的又說下去,她和母親小學同班,母親從小就很美麗,又很會唱歌,在學校很出風頭,她回憶母親最會唱的一首搖嬰歌,她在電話的那端低聲的哼起「搖啊搖……」我告訴她,我記得小女孩時,母親曾帶我去過她家,她因為嫁給一位小開,婚後生活較母親優渥許多,不過,兩人的小學同窗情誼仍維續了一輩子。
聽著她因生病而力道不足的哼著搖嬰歌,我不免會想到母親的另一位小學同學,她在母親停靈時的一個夜晚,出現在冷清的街道,由於她的氣質高雅,正在守靈的我們,不免對她多看了幾眼,但見她筆直的朝我們走過來,沉默的走進靈堂,待我們遞過香枝,才看到她的臉上掛滿了淚,她輕聲的喚著母親的名字說,「我來看你了。」之後,她對著初識的我們自我介紹說,她是母親的小學同學,原先在上星期和母親約好一起去唱歌,後來沒約成,沒想到竟天人永隔了。
因為空襲的緣故,母親讀到小學三年級就中輟學業,後來因家境十分貧困,沒有機會再重返校園。只有接受過三年小學教育的母親,不但國語文讀寫流暢,日文亦然。先前只曉得母親是一個聰穎的人,沒想到,在她過世後,才又認識了她終身交往的同學。母親過世後,先生曾問我母親是彰化的那裡人,我困惑的說,「不知道」。後來問了阿姨,才知道母親生長在彰化市富貴里的竹頭腳。我和母親生活了一輩子,感覺十分親近,但在她走後,才意識到,她的生命有好多的面相,是我所不了解。
遊覽車的前頭,叔叔猶在追憶母親和父親的戀愛史,唱作俱佳的表述,逗得大家開懷。然而並沒人忘卻我們正在等候母親真正煙化的時刻,不時有人在看腕表,然後一聲「差不多了」,大家便又默契十足的下了車,往火葬場走。
場內幾位男性的工作人員嫻熟的將焚化過的石膏色骨骸裝進罈裡,哥哥謹慎的接過了母親的骨灰罈,我撐著黑傘在旁邊護著,然後一群親友又各自喚著母親的稱謂,「我們要走了!」、「要過橋了!」就這樣又從青蔥的山區,進入水里,穿過河流,通過山洞,一路指引著母親的魂魄跟著到了台中。
父親過世後,葬在台中東海墓園,母親生前即交代身後骨灰要放在墓園裡新建的骨塔,我們踏進了中庭挑高的骨塔大廳,大廳寬敞明亮有如旅店,環著中庭是一間間祭拜廳,祭拜廳的正中央是一個大型螢幕,可以播出亡者的照片以供家屬追思。
我們先在大廳的沙發上小歇,並且啜飲著自助的咖啡,怡人的環境,讓大家共同覺得真是一處不錯的安息地。
佛事圓滿後,法師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到這個有如大廈的骨塔樓,又問母親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我說母親知道許多事,雖然她只讀過三年的小學。就像她的另一位好友重貴常常說:「你母親懂的事真多,我都叫她楊博士。」然後又感謂的說:「你母親突然過世,是我人生最大的損失。」阿姨也常提起,她們少女時,家境非常貧窮,但外婆卻仍捨得讓母親去學舞蹈。母親擅歌、擅舞、聰慧,人又高雅美麗,這是她的青春伴侶對她的共同印象。但我印象中的母親卻不然,她要用木屑在大←中升火,烹煮大家庭四代同堂的飲食,她過度大方,常捉襟見肘,她是一個以家庭為重心的傳統女性,不過有一點共通的印象是,母親一直得到別人的讚美。
我告訴法師說,母親會選擇安葬在這裡,是因為父親也葬在這墓園,而且這裡可以喝咖啡,至於當初母親為何會決定將父親葬在這裡,是因為風流英俊的父親生前很喜歡從彰化到台中來跳舞。由於父親非常疼愛我這個么女,還曾帶著少女的我,出入過台中的各大舞廳,驕其舞女。深愛父親的母親卻對這些事一笑置之。
將母親的骨灰安放後,我們魚貫的上車準備回彰化,車子開動不久,哥哥指著右邊一排排整齊的墓區說,父親的墓就從這裡進去。父親過世多年,他的身形還歷歷在目,但我已不復記得他的墓區了。
車上的親友開始聊了起來,說著父親在這裡還可以繼續去跳舞,愛漂亮的母親也可以在台中逛街、喝咖啡。經過了一天的送行,此刻車上的氣氛輕鬆起來,大家繼續想像著以後父母親在台中,會再做些甚麼事,感覺他們的生命並沒有真正過往,而是在我們的追憶中延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