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間的迷思與衝突藝術家往往獨具超然的表象和敏銳的洞察力將個人痛苦的生活經驗化為客觀的觀賞和思惟並透過藝術的表象為個人和人類指出解脫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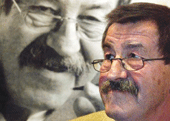 回顧人類社會過去近百年來的種種變遷。從一九三○到一九四五年的這段戰亂的歲月,無疑是上世紀人類所共有的痛苦記憶。然而,無論生活墮落到何種地步,人們總有「藝術」作為捍衛人類精神文明的最後堡壘,因為,誠如尼采所言︰「唯有她,才能將那股對於存在之恐怖和荒謬的厭惡感轉變為表象」。面對世間的迷思與衝突,藝術家往往獨具超然的表象和敏銳的洞察力,將個人痛苦的生活經驗化為客觀的觀賞和思惟,並透過藝術的表象,為個人和人類指出解脫的方向。
回顧人類社會過去近百年來的種種變遷。從一九三○到一九四五年的這段戰亂的歲月,無疑是上世紀人類所共有的痛苦記憶。然而,無論生活墮落到何種地步,人們總有「藝術」作為捍衛人類精神文明的最後堡壘,因為,誠如尼采所言︰「唯有她,才能將那股對於存在之恐怖和荒謬的厭惡感轉變為表象」。面對世間的迷思與衝突,藝術家往往獨具超然的表象和敏銳的洞察力,將個人痛苦的生活經驗化為客觀的觀賞和思惟,並透過藝術的表象,為個人和人類指出解脫的方向。
遺忘的歷史惡夢
一九九九年獲得諾貝爾桂冠的德國二十世紀大文豪君特‧葛拉斯(Gunter Grass,1927~),在其著名之《但澤三部曲》 (Die Danziger Trilogie),包括長篇小說成名作《錫鼓》(Die Blechtrommel,1959)、中篇小說《貓與鼠》(Katz und Maus, 1961) ,以及長篇《狗年月》(Hundejahre, 1963)三部小說中,就以自己出生成長的故鄉波蘭但澤(Danzig)─ 及其市郊朗富爾(Langfuhr)為敘述的出發點,用杜撰的故事與人物,描繪在二次大戰及其前後的期間支撐整個德國第三帝國的小市民生活動態,重現那一段使後代德國人為之蒙羞,而寧願將之遺忘的歷史惡夢。
在葛拉斯小說的虛構故事裡,到底反映了多少的歷史真實面和作者參與納粹的慘痛經驗?杜撰中含有多少寫實?而虛擬的人物造型中又有何文學的象徵意義?無疑是耐人尋味且值得探討的問題。筆者有幸於一九九六年在德國巴伐利亞小鎮Weilheim聆聽葛拉斯朗誦作品,並對這些問題作了一些探討。
葛拉斯是波蘭但澤人,他是位兼具了多面才華的藝術家。早年從事文藝創作之初,他曾經徘徊於小說家和雕塑家的兩難抉擇。但自其長篇小說的處女作《錫鼓》問世後,葛拉斯一砲而紅,震驚文壇,使他走上小說創作之路,也奠定了他在現代德國戰後文學上的地位。
「戰後文學」是葛拉斯《錫鼓》這本近八百頁的暢銷書,以及隨後陸續發表的中篇《貓與鼠》和長篇《狗年月》共同的屬性。這三篇小說,出版時間前後固然相隔四年之久,但其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都發生在作者的出生地─但澤(今名格旦斯克,中世紀原為漢薩同盟Hansa之商業城市,後屬東普魯士,居民多為說德語之日耳曼人。因具出海港之優勢地理位置,波蘭建國後屢遭列強侵佔。一次戰後,但澤成為當時歐洲列強共管之自由市。一九三九年復為納粹德國占領,至一九四五年戰後始歸還波蘭),不同故事也都由此開始敘述,鄉土情感,留給他太多的回憶。此外,從三篇小說中共同的時空範圍(都在第二次大戰前後約五十年間),及回憶的過程、敘述情節的先後次序和人物的重疊來看,三部小說也明顯的都彼此互有關聯,是依著相同題材和主題構思出來的作品。
悲慘命運正是小說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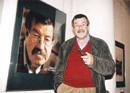 《但澤三部曲》三篇小說皆是以回憶往事,敘說故事的方式,虛構寫實、設喻諷刺,將歷史事件和自傳題材融入杜撰的故事情節,藉批判納粹英雄崇拜的狂熱,描述納粹法西斯的惡形惡狀,同時並分析支撐此滔天罪行的共犯結構─德國小市民(Kleinburger) 階級的盲從,及其道德淪喪的情況。前者如《貓與鼠》中,皮倫茨回憶追悼馬耳克因英雄狂熱的幻滅而自沈,《狗年月》中藉著人民對元首愛犬盲目的崇拜,嘲諷納粹政權下諸多荒誕鬧劇,象徵納粹政權的非理性,並暴露當時社會的外在環境和人的內心世界所隱含的矛盾。後者如《錫鼓》中畸形侏儒奧斯卡,因怕見昏暗、冷酷的世界而拒絕長大,寧用小人物卑下的眼光透視大人世界,從反面觀察解構,擊鼓控訴大人們的亂倫敗德,諷刺小市民搖旗吶喊的愚昧與瘋狂。
《但澤三部曲》三篇小說皆是以回憶往事,敘說故事的方式,虛構寫實、設喻諷刺,將歷史事件和自傳題材融入杜撰的故事情節,藉批判納粹英雄崇拜的狂熱,描述納粹法西斯的惡形惡狀,同時並分析支撐此滔天罪行的共犯結構─德國小市民(Kleinburger) 階級的盲從,及其道德淪喪的情況。前者如《貓與鼠》中,皮倫茨回憶追悼馬耳克因英雄狂熱的幻滅而自沈,《狗年月》中藉著人民對元首愛犬盲目的崇拜,嘲諷納粹政權下諸多荒誕鬧劇,象徵納粹政權的非理性,並暴露當時社會的外在環境和人的內心世界所隱含的矛盾。後者如《錫鼓》中畸形侏儒奧斯卡,因怕見昏暗、冷酷的世界而拒絕長大,寧用小人物卑下的眼光透視大人世界,從反面觀察解構,擊鼓控訴大人們的亂倫敗德,諷刺小市民搖旗吶喊的愚昧與瘋狂。
葛拉斯一連串的戰後文學小說創作,似乎駁斥了著名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學家和文藝批評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名言:「奧施維茲之後,吟詩創作以令人無法忍受!」(Das Schreiben von Gedichten ist nach Auschwitz unmoglich geworden)(譯自Hermann Korte: 25)奧施維茲是德國惡名昭彰集中營所在地,現已成為納粹政治迫害和猶太大屠殺慘劇的代名詞。天生硬骨頭的葛拉斯不向悲慘的命運低頭。他認為他以及他那一代的作家,即使不是奧施維茲的兇手,也是屬於兇手的陣營(Grass: Gegen die ver-streichende Zeit, 51)。尤其他本人就讀中學時就遭納粹的蠱惑,加入希特勒少年團。一九四四年入伍當砲兵,旋即受傷被俘,成為德國軍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
他父親是曾加入納粹的德國人,母親是波蘭人,故有身為波蘭人的受害,又有德國人加害波蘭人的罪惡感。戰後家鄉但澤歸還波蘭,他又被迫離鄉背井,其悲慘身世一如《錫鼓》中的奧斯卡。這些刻骨銘心的經驗後來成為他寫小說的題材,是可以理解的。而反抗、控訴奧施維茲和納粹德國自然就成為鞭策他創作的動機和主題,這也是他在〈書寫在奧施維茲之後〉一文中所作的自白與聲明。可見葛氏的美學出自罪惡意識和社會正義感構思出來的。正如他的朋友,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鮑爾(Heinrich Boll, 1916-1985)所說:「書寫,意味著參與自己的時代所發生的時事」。
葛拉斯也認為文學必須要能反映政治社會的實況,但並不是搞政治。「搞政治」照他的看法是身為公民應主動參與的工作,但不屬於文學範疇。文學透過虛構故事所展現的是另外的事實映像,正如他所說,是種比「現在與過去的歷史實況更真實的面貌」。基本上,他也認為歷史是荒謬的,因此他能接受卡謬荒謬哲學的論點,並效法杜柏林(Doblin)以書寫小說來超越歷史。
小說 打破傳統禁忌
我們不妨以《錫鼓》為例,來了解葛拉斯小說的杜撰與寫實。整體而言,葛拉斯的戰後文學作品,包括《但澤三部曲》以及一九七二年以前所發表的小說,如《局部麻醉》、《蝸牛日記》,對德國第三帝國所造成的歷史浩劫所作的描繪,猶如一面照妖鏡,使德國法西斯的邪惡無所遁形。小說揭露政治、宗教和社會倫理的瘡疤,打破傳統禁忌,所造成的社會衝激,有助於後世人對過去荒謬行為作深入省察。瑞典科學院對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評語:「他在輕鬆活潑的灰色虛構故事中顯現了歷史已被遺忘的臉孔」,似乎特別針對《錫鼓》作註,指出了這部文學小說之社會寫實功能。
讀者或許會質疑,《錫鼓》中,作者杜撰一個生下來即聽懂大人說話之小孩奧斯卡,既能拒絕長大,又具有唱碎玻璃的本領,並且隨身帶著他的鼓到處敲打。這個畸形的侏儒形同他另一部小說裡那隻會說話的鰈魚,以及其他諸多由貓、鼠、狗的比喻來象徵怪誕不經的人物,豈不流於科幻童話,哪算什麼寫實?此話固然沒錯。但文學的表象不同於一般紀實報導或抽象概念的表述。主觀的思想或抽象的概念須化為具體故事情節作客觀的表達,荒唐的人生世相和荒謬的事物更需要透過杜撰的故事來影射。葛拉斯本人,是抨擊德國基民黨及保守派不遺餘力的民主鬥士。儘管其批評時政的言論再激烈主觀,但在文學創作中卻能保持藝術表達的客觀性,他擅於杜撰故事,將內心的感受客觀地敘述出來。
葛拉斯的十多部小說,幾乎清一色用「我」第一人稱敘述。然而,這個「我」,卻是如同《我的世紀》書上第一句話所說的,是「替換了的我」,是像奧斯卡、皮倫茨之類的杜撰人物,不是作者本人。換句話說,作者不介入情節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隱沒在故事和人物背後,保持超然的敘述立場,以便能從旁揶揄、諷刺、批判所敘述的事物。作者欲藉文學的杜撰,重新塑造歷史,顛覆歷史,尤其是顛覆納粹那段荒謬的歷史!因此,侏儒奧斯卡必須不停地猛敲錫鼓,不斷敘述。
《錫鼓》成為他一生的避難所
儘管葛拉斯的政治意識型態相當背離德國唯心主義的傳統,儘管他的小說風格帶有幾分如他所說的杜柏林小說的「未來主義的成分」,但他在第一部小說中卻以相當完整的小說形式和主題架構,將錫鼓描寫為敘述藝術的象徵物,用來對抗外在荒謬世界,或彌補不能獲得滿足的生活欲望 。這種藝術與生活對立的二分法,使《錫鼓》作者無形中墮入他所憎惡的唯心主義的思惟領域。譬如小說提到,敘述者奧斯卡出生時心智發育已完成。為閃避這殘酷的世界,他急欲返回娘胎,然而臍帶已被剪斷。在無可奈何之際,遙聞媽媽許諾在他三歲時送給他一面錫鼓。為了這面鼓他才有勇氣活下去。他說:「唯有那面遙遙在望的錫鼓才使我沒有更強烈地表達出重返娘胎倒立位置的願望。」於是這面象徵藝術的錫鼓遂成為他一生的避難所,也是他避開外界成人惡劣行為的內心世界。
他之所以痛批浪漫唯心主義及其所代表的德國思想界巨人,而欲佣侏儒以小觀大的眼光解構它,甚至用動物的本性和只求物慾享受的小市民的感官需求來取代它,主要因為德國十八、十九世紀唯心論哲學和文藝思想從康德、赫德、歌德、席勒到黑格爾、斐希德,是在德意志軍國主義政治社會背景下發展壯大,帶有國家主義色彩,後來成為孕育納粹(即「國家社會主義」的簡稱)的溫床。德國人坐視納粹殘害無辜、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當時即連教會也一併同流合污,教廷與納粹德國簽訂合約,成為共犯。故天主教宗教信仰與唯心的超越精神在小說中一併遭批判詆毀。也因為這種批判態度,使《錫鼓》一直蒙上誣衊神明、褻瀆上帝的罪名。
葛拉斯在但澤就讀中學時曾遭納粹蠱惑,加入希特勒少年團,後於一九四三年正式入伍,旋即淪為戰俘,成為德國軍國主義的犧牲者。《但澤三部曲》中的每一個篇章都充分地表達了他對軍國英雄崇拜的反感。我們可以說,葛拉斯當初動筆撰寫小說的動機乃出於德國人參戰者的罪惡感。而此罪惡感的表述卻是與五、六十年代德國人拼命要排除納粹惡夢、掩滅共犯罪狀的思惟方式背道而馳的。他的小說用詼諧的杜撰故事,結合豐富人生經驗、奇聞軼事和神話幻想,將歷史寫實和作者對人生社會批評融入完整的敘述藝術。
(摘自葛拉斯《但澤三部曲》的主題和敘述架構。《中外文學》30卷,第4期,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