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英國製造——英國文化協會當代藝術展1980—2010」先後在成都、西安、香港和蘇州展出,看過的朋友有種種意見。我沒有置喙,過後印象也不深刻,卻老是想起去年初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看的「英國現代雕塑」展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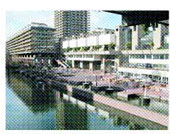
當天一早我就坐巴士到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然後在肯辛頓公園看了印度雕塑家Anish Kapoor的公共藝術作品。早上的空氣清新,我再漫步到旁邊的海德公園,看看學員騎馬行經天鵝喝水的湖畔、嚵嘴的小松鼠翻弄垃圾,輕鬆地度過了一個微寒早晨。
沿著Piccadilly,就抵達倫敦皇家藝術學院了。當天看「英國現代雕塑」展覽的人不少,因為有學生參觀,老師除了簡介歷史,也不斷問學生「這是雕塑嗎」,好像要引發他們思考。
英國二十世紀最著名的雕塑家大概是Barbara Hepworth和Henry Moore,展覽中選取了他們的名作。前者的作品較抽象,後者相對具體,也為香港人所熟悉,中環的交易廣場就有他的名作《雙橢形》(Double Oval),可是匆忙的路人大多無暇一顧。
英國當代雕塑不時衝擊原有的藝術理解,雕塑愈發傾向像裝置藝術,對空間及媒體運用的探索,大於對形式本身的追求,Victor Pasmore和Richard Hamilton的《一個展示品》(An Exhibit),難得對兩邊都有關注,整個空間被許多垂吊的顏色/透明板塊切割,空間徹底抽象化之餘,也思考了形式的秩序及建構。
著名的英國青年藝術家(YBAs)Damien Hirst和Sarah Lucas,現在都不是青年了。Sarah Lucas的《手提吸菸空間》(Portable Smoking Area)很簡單,一張椅和一個可以升高放下的木箱,如要抽菸,一放下木箱罩著頭部就是私人空間。Damien Hirst的《讓我們今天去野餐》(Let's Eat Outdoors Today)是展覽中最矚目的作品,兩間互通的巨大玻璃房,一邊是燒烤爐,肉上養著成百上千的蒼蠅;另一邊是人們吃剩的野餐食物,大群蒼蠅在此開大餐,但玻璃房內又有一個滅蠅器,蒼蠅一踫就死。這個令每一個人震驚的(雕塑?裝置?)作品,反思了文明習慣、悠閒生活的陰暗面,也教人直面可怕的現實,甚至出生、朽壞、滅亡循環的不變道理。
下午,我從皇家藝術學院轉往瓮城藝術中心(Barbican Centre,見右圖),當天沒有甚麼特別的展覽,但我很喜歡那個地方。不單是建築的現代感與粗野感,以及鮮紅色的郵箱是我小時候所常見,更由於房屋與藝術場地在此渾然結合,跟香港慣見的住宅與商場密不可分,截然不同。人除了是消費者,還有藝術與精神生活的需求,我想像圖書館、音樂廳、電影院、展覽廳,在街角路旁、在天橋上、在車廂中、在日常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