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寺門早早大開,從寺裡出來的參拜者,不管老少,手上都已有滿載的收穫,我探頭一看,這熱鬧非比尋常,早把當初的計畫拋到琵琶湖裡了。知恩寺,我來了!
徘徊在十字路口,正為方向的抉擇費心時,抬頭看到路標上的「東大道」,我住東山三條時,不就在這條大道上晃過來繞過去的嗎?原來它綿延到百萬遍來了,它的盡頭在哪裡呢?就從百萬遍走它一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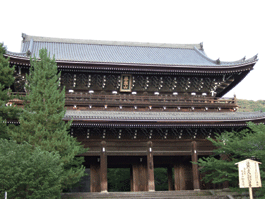
哪知才走幾分鐘,來到了知恩寺寺門口,今天的寺門早早大開,而且才到九點,早已人聲鼎沸,從寺裡出來的參拜者,不管老少,手上都已有滿載的收穫,我探頭一看,這熱鬧非比尋常,早把當初的計畫拋到琵琶湖裡了。知恩寺,我來了!
一進寺門,看到的是搭著帳棚的小小攤位綿延好幾排,有些攤位上方,掛著一紙類似許可證或是收據,上面標示「手作市集」,然後是此攤位的主人名姓,下方則標著三○○○日幣,應是一個攤位的日租金吧?發給單位是京都市府。比手劃腳問了人,才得知原來這是知恩寺每月十五日的手創市集出店日。日本有許多寺院,都有這樣的弘法市集,記得壽岳章子那本「千年繁華」的書中,曾提及她小時一家人逛東寺弘法市集的往事,說那是京都此等市集的始祖。後來回去京大一查,才知道原來附近的北野天滿宮,熊野神社……等,也都在不同的日子裡,有這樣的市集,可惜有些已經錯過,北野的二十五日,我人已經在飛機上了。
走在人群裡,才看第一家,我顯然已經淪陷了,不知從哪裡突然冒出了這麼多遊客,而我看到的第一攤,賣的正是用乾燥的各式松果,串集成的藝品,有小松果的胸花,有大松果的乾燥花型擺飾,極具巧意,我對這攤子頓起相惜的情意,無論到哪裡旅行,只要經過栽種松樹的地方,我一定要彎著腰在那片土地上搜尋,千方百計撿拾幾個當地的松果,放在行囊裡偷渡回家,家中客廳那盤松果,因此有各個來處:記憶中最早的一顆,是到孩兒學校,參加他大學畢業典禮時,在水木清華的校園撿拾來的,揀完松果已經下午,還沒看見典禮的任何動靜,孩兒才急急告訴我們,原來典禮是晚上七點才開始,而我們弄錯時間,早買了七點回台南的車票,這顆松果見證了一個烏龍家庭的脫序演出;相繼加入的有黃山、奈良、楓丹白露、聖彼得堡酘酘等,各地不同顏色,不同樣態的松果,一個個幫我記憶了南來北往的天涯羈旅。去年到佛州,把小叔後院的松果放入行囊時,也正是揮手與他們告別的時候;那些牡丹花型的松果,更是紫霞遠從紐西蘭基督城千里迢迢帶回,之中承載著濃郁的情意。我在這松果藝品攤子前,顯然駐足的失神了,左推右擠的人潮,終於把我的思緒拉回。
日本人對於手工藝品的抬愛,只可用「沉醉」來形容,這個每月一次的市集,為愛創作及愛收集手工製品的人,提供了一個平台。我看許多攤位的主人,還來不及做生意,已經迫不及待的跟隔鄰的攤主,熱絡的交談,彼此互相讚美作品的精良巧思,順便交換製作的心得技巧,好像今日是提著他們自己的作品當「伴手」,來互相拜訪,完全不在意上門的顧客多不多,讓站在一旁的我,也跟著他們沉浸在彼此的笑語裡。逛這種市集,沒有任何心理負擔,每走到一個攤位面前,店家就笑開一張臉,直跟你鞠躬,感激你光臨他的攤子,還拿著他的產品,直跟你解釋他產品的特色,我其實只能半猜他們的話意,但實在留戀他們那樣溫婉誠意的態度,以及對自己作品的疼惜與自信,因此一攤攤聽,一次一的微笑點頭,跟著驚嘆幾聲。有些攤子除了賣成品,店家還心細的把製作過程、方法寫下,畫上插圖,製成漂亮的卡片,夾在物件裡,讓買到的人打開之後,有無限的驚喜和幸福的感覺,這種生意,無異於和顧客們一一交心。
有許多攤子的店家,不乏上了年紀的人,尤其賣手工漬物的攤前,常常可以看到穿著圍兜的老人,臉上的滄桑,和缸中漬品,同樣有著歲月發酵過的韻醞。有位頗有年紀的婦人,坐在攤子後的座椅上,專注的用碎布縫製拼布,手上的針線密密的上下,拼好的作品,平整美麗得一如熨燙過,引來一陣陣的喝采。京都有許多各行各業的達人,都是像眼前的這位,跟你擦身而過時,不過是尋常巷陌裡偶遇的老婦或耆者,而他們可能為了釀好一缸菜,烤好一盤手工餅,甚至做好一支好掃地的掃把,而窮其一生,用生命賭上。
我陸陸續續走過賣藍染的衣舖、賣手拉胚的陶瓷店,賣金工的日用品店,女孩子們看來較擅長烘烤餅乾,鉤桌巾,作布娃娃,手提袋酘酘,甚或有人用各式素紙,當場繪製顧客指定的專屬卡片,中午時,手烤糕餅攤前,大擺長龍的人潮,害店家不斷抱歉讓顧客久等,而參雜在人潮中,最常聽到的是迴盪在微風中的一聲聲「阿哩嘎多」。
離開市集時,已經下午,但湧入的人仍然一波波,聽說這市集是採取當天登記的方式,外國的旅人也可以申請, 想起前陣子看了張尊禛寫的那本「台灣老字號」,裡頭介紹了三十二間台灣的各行老店,裡頭不乏百年守護 一味的傳統行業,多麼希望這些堅持幾世或拋擲一生,因而讓台灣這麼美好的東西得以保留下來的達人們,也能有一個永久的舞台,讓他們能盡情揮灑他們究極的手藝,也為一代一代的子孫留些往後回顧時的舊時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