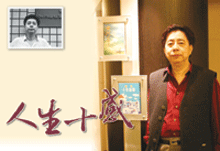 二十七年來,透過他的手,製作了將近五百四十種文學書;而他自己也是一位寫作者,五十年來,寫了近三十種書。隱地說:度過七十個春天,心中充滿感恩,雖然,就「菱形人生」來說,他的歲月已進入冬的國境,但卻時時回憶著自己春天的快樂,並咀嚼著春天的滋味。自己也立刻變成七十歲少年。
二十七年來,透過他的手,製作了將近五百四十種文學書;而他自己也是一位寫作者,五十年來,寫了近三十種書。隱地說:度過七十個春天,心中充滿感恩,雖然,就「菱形人生」來說,他的歲月已進入冬的國境,但卻時時回憶著自己春天的快樂,並咀嚼著春天的滋味。自己也立刻變成七十歲少年。
今年5月,隱地出版他第38本新書《我的眼睛》,封底內外,他放上20年前與現在的兩張照片,焦點都在眼睛。 隱地有一雙愛看書的眼睛,從小就是愛看書,後來變成一個作家暨做書的人。成立爾雅出版社33年以來,6、7百本書從他的手中印了出來。
隱地有一雙愛看書的眼睛,從小就是愛看書,後來變成一個作家暨做書的人。成立爾雅出版社33年以來,6、7百本書從他的手中印了出來。
作家曉風曾替他算過,她說超過6億個方塊字從隱地的編輯台上流過。隱地還有一雙看愛電影的眼睛。從10歲到如今,看了一甲子的電影。隱地說,最初看電影,就是看電影,現在看電影,是因為電影成為他的人生學習和社會大學。看電影使他成為一個生命的思索者。
幸虧有一雙閉目養神的眼睛
人生有太多不如意的事,「幸虧,我有一雙閉目養神的眼睛,讓自己的腦海一片空白。當我想到自己從事的文學出版事業逐漸日暮途窮,當我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終於揮筆而成的書冊,連區區2千本也銷售不完,幸虧我有一雙閉目養神的眼睛。只要我把眼睛閉起來,一個純靜的世界就像嬰兒般躺在前面。」
已度過70個寒暑的隱地,在56歲那年遇到詩。年輕時,隱地從來不曾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一個寫詩的人,且出版了《法式裸睡》、《生命曠野》《一天裡的戲碼》3本詩集。詩人向明認為隱地的詩最大特色是「天真和出人意表的趣味」。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俊曾花了一番時間研究隱地的詩,他認為,隱地的詩充滿人生哲理的品質風貌,「當人們被現代詩歌的含混和玄妙弄得張惶失措、敬而遠之的時候,隱地的詩恰如一股清新的涼風,吹拂向人們那已被現代生活震撼得疲憊不堪的心靈,而當人們靜下心,沉潛進隱地詩歌的藝術世界的時候,他們又會發現隱地的詩其實更像一盅清淡而又悠遠的新茶,沁人心脾,耐人尋味。」
從小說家的國度跨向詩人國
隱地的第一首詩是半夜起床打蚊子的偶然之作;那隻在深夜嗡嗡叫個不停的蚊子,擾得他無法安眠,遂起身打蚊子,沒有想到竟激發了他寫詩的靈感:「法式裸睡/是睡覺的一種方法/法式田螺耟是一種吃田螺的方法/天下什麼事都講方法/譬如擺脫丈夫的方法/吃西瓜的方法/以及做愛的一○一種方法/在一千零一夜裡/睡著是為了醒來/睡不著呢?/你就做詩/或者打蚊子/打蚊子/是為了睡覺/睡著了/身體是蚊子的幸福天堂!」
隱地完成「法式裸睡」這首詩作,並沒有立刻寄出去,而是放在抽屜,偶而拿出來讀讀,隔了一陣子他才寄給寫詩的朋友,看看是否能發表。張默沒有正面答覆,只說以後還可以寫出更好的東西,讓滿心期待的他頓時失去信心。後來有人建議他不妨投給聯合、中時的副刊看看,也許會刊登,他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投給中時,很快就登了出來。彷彿打了一針強心針,很快他又寫了3首詩,也得到聯副主編陳義芝的好評,並歡迎他從小說家的國度跨向詩人國。從此一首首的詩從隱地的筆尖流出,也持續在報紙副刊發表。
我們的世界早已不安靜
寫詩使隱地從出版的頹勢中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每一首詩的發表都帶給他快樂,寫詩也讓他從弱勢觀點看問題,逆勢操作,使他的人生境界更上層樓,回憶這段寫詩的日子,隱地感性的說:「人生在世,庸碌一場,幸虧有詩──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才變得豐富而有趣。任何硬梆梆的場面,如果有了詩,一切就會改變,鐵血裡的柔情才會流瀉出來,英雄流淚也是一種詩作啊……人生無詩會無趣。」
認識隱地的人都知道,他沒有手機,也不用電腦,他的稿件應該是少數主編還可以得到的手稿寫成的。隱地非常懷舊,任何一本他寫的書裡,不論是小說、散文、評論還是詩,都透出許多懷舊之情,讀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下面就是一個例子。
在電腦排版尚未出現前,出版品都是採用人工鉛字排版。1982年,電腦排版上市了,初期的電腦字體極醜,但價格便宜,搶了不少鉛版印刷的生意。幾年後電腦軟體突飛猛進,成本又驟降,使得鉛字排版廠一家家不支倒地。1994年,為爾雅印書已10餘年的印刷廠,要結束鉛版撿字和印刷,鑄字、排版、鉛字印刷這一行已被時代浪潮淘汰。隱地相當不捨,為了趕搭鉛字末班車,他特地趕著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叫《翻轉的年代》,在序文裡有這樣一句話:「我們的世界早已不安靜。」
懷舊又充滿時代的嗅覺
隱地擁護鉛字書是有原因的,多年來他始終認為,鉛字給人的感覺是厚重、真切又美麗,觸摸時有凹凸的感覺,雖然印刷過程很繁複,但因為有人參與,因此充滿趣味,也加深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電腦排版無論字體如何選擇,總有一種飄浮和不實在。在鉛字排版的那段時間,隱地經常跑印刷廠,忙碌起來還會睡在廠內的紙上,隨時等著看打樣,他也認識許多印刷廠的朋友,只要一通電話就可以解決不少問題。
事實上,除了懷舊,隱地也很有時代的嗅覺,隨時發生了什麼事,他都關心而且有意見,常常很強烈,一定要一吐為快,比年齡小他一半的人還要激動。「不要以為他不成熟,他的言語短潔有力,卻透出人生厚實的歷練。」與隱地相交多年的的作家亮軒這樣形容他。
隱地對時代變遷對人類造成影響的題材,特別敏感,不時寫出令人回味無窮的文章,像:「資本主義和科學家已經把世界一切為二,有些人跑得太快,有些人落後太多。快和慢的節奏,亂了現代人腳步。其實兩種人可以互為彌補,中間連接起來的是,需要愛與和平。不過歷史告訴我們,人性之中充滿爭鬥,世界看來就像日出日落,黑暗和光明就這樣交替著,所以每個人活在這個脫序的社會,要聰明學到的是,在磨難挫折的人世裡培養自己嗜好,有嗜好的人,可以暫時忘記人間的傾軋,一天一周或一個月中,總要有一段自己的快樂時光。」
在他身上有點時空錯亂
隱地表示,一個完全沒有嗜好的人,自己感覺活得好累,在別人眼裡也覺無趣。人只活一次,要活得不虛此行,就一定要有自己的嗜好,什麼嗜好都可以,只要你自己覺得開心。人要努力,能做出一番有意義的事業固然好,如未能闖出一片天,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也沒什麼不好,重要的是要設法活得快快樂樂,死而無憾。
亮軒表示,很難把隱地歸類到什麼樣的人物中去,在隱地的身上,有點時空錯亂。這個人10歲才開始認字讀書,看他的生平,誰也不能否認充滿了磨難,但是他的品味卻比一般人要好得多。要是說他處處講究,倒也看不出他有任何一點的紈←氣息,看他做那麼多的事情,寫那麼多的作品,他應該是文壇最勤勞的人之一。「他年過70,說出來都沒有人會相信,不一定是因為看得出來還是看不出來,反正現在年紀大了真能讓人看出來的也不多,但是他的活力跟智能還有學習吸收的能力,大多數的少年家不一定比得上,這是大家難以相信他有那麼大的年紀的主因。」
少年的傷是如此深且劇
文藝圈的朋友看隱地,總是一派溫文儒雅,懂得生活,是一個品味不凡的人。直到2000年,隱地陸續發表一連串告白式的文章,傾吐隱藏心中40中年的心事,連相交多年的老友看了都不免大吃一驚。王鼎鈞說:「與隱地相交30多年,全然不知道他少年時代的種種艱苦。」白先勇讀了這些文章,直覺和隱地以往雲淡風清的散文風格大不相同,就如同結集成書的名字《漲潮日》,暗潮洶湧,起伏不平,「因為作者在寫他自己徬徨少年時的一段痛,少年的傷是如此之深且劇。」
1947年,10歲的隱地從大陸來台,投靠早先抵台的父親,當時他還目不識丁,在大陸正準備下田插秧,母親在緊要關頭帶他來台灣,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父親原本在北一女教書,也經營生意,生活過得還不錯。可惜識人不明,錢財全部被騙光,最後連教職也丟了,終身潦倒。
母親不耐貧窮,離家出走,少年時的隱地,擺盪在父母之間,經常衣食無著,三餐不繼,甚至飄泊流浪,居無定所,青澀年紀早已飽嘗人生辛酸委屈,對父母的怨恨,當然不止車載斗量,所以等了40餘年,最後經過了解、諒解的艱難過程,終於與人生取得最後和解,才開始把心中的積怨與隱痛化成感人的文字,白先勇認為,「對作者隱地來說,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療傷手術。」
在不斷搬家的流浪日子裡,隱地靠著寒暑假去賣報紙以及送煤球來賺取學費,這些不愉快的青少年經驗,對他接觸文學,反倒成了有利因素,隱地也承認,貧窮和不正常的童年,對寫作人來說,有時也是一種寶礦。 老師指引路 寫稿也可賺錢
隱地的閱讀是從連環圖畫開始的,接著是「東方少年」、「學友雜誌」、「格林童話」、「伊索寓言」、「苦兒流浪記」,女師附小3年級,已成為班上說故事的高手,5 年級開始在國語日報寫「學府風光」。讀新莊實驗初中,碰到生命中第一位貴人──國文老師姜一涵,他知道隱地的特殊遭遇,給他加倍的關心,並鼓勵他投稿,「他指引我一條路,原來寫稿也可以賺錢。」
隱地表示,不畏窮苦,也懂得窮苦反而可以磨練一個人的意志,「要不是姜老師的牽引,我可能變得自暴自棄,一個在貧窮境裡長大的孩子可以奮發向上,也可以往下沉淪,一念之間,常常是不同的下場。」
從學生園地寫到「自由青年」雜誌,主編梅遜是他生命第二位貴人。由於長期在「自由青年」寫稿,也出了書,引起文星雜誌蕭孟能的注意,主動找他主編一套青年作家選集,之後,又為林海音主編的「純文學」雜誌擔任助理編輯,這一段經歷對他日後主編「青溪」雜誌、「新文藝」月刊,甚至「書評書目」雜誌都有很大的幫助。
1975年,創辦爾雅出版社。隱地表示,爾雅能夠走過33年,仍然屹立不搖,就是因為在「純文學」月刊一年,從林海音那兒一點一滴學她的勤奮,學她的幹練。出版之餘,隱地的筆也沒有停過,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寫作、近50年的歲月,隱地從未離開文學這個園地,明年還準備推出另一本新書。
永不停筆的背後,也有讓隱地憂心的事情,面對每隔一陣子,就會有人出來說:「文學已死」,一度讓他也很傷感。文學真的死了嗎?
可以偶爾氣餒 但不能屈服
對於這個問題,隱地有一套看法,他說,多年前,我們曾經擁有「文壇」、「寶島文藝」、「台灣文藝」、「現代文學」、「純文學」、「書評書目」等文學雜誌,如今在消費文化襲擊之下,雜誌雖然愈出愈多,和文學相關的卻愈來愈少。「文學如今已成圍城,被包裝紙攻陷,淹沒在淺灘一角,作家手中的一支筆,大都已不再方格紙上筆耕,而改用嘴、用臉,向媒體寵兒進軍,成為電視人。眼前甚多創作者頗為無奈,稿件寄到出版社,出版社說了一大堆理由,最後是稿件又退了回去。」
隱地認為,文學當然不會死,「只是文學的路是愈走愈窄,文學成為小眾,或許要等到小眾的覺醒,才能走出另一個文學的春天。」
自認度過70個春天的隱地,心中充滿感恩,雖然,就「菱形人生」來說,他的歲月已進入冬的國境,但卻時時回憶著自己春天的快樂,並咀嚼著春天的滋味。……只要望著窗前美景,他就立刻變成70歲少年了。因此,儘管文學成為小眾,文學書不好銷,他也要一直為文學努力下去;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庫存的新書一本一本流出去。
隱地說,就算倉庫裡的書真是一座又一座的山,「我也應在群山裡歌唱,而非在谷中哭泣!一個老文學人可以偶爾氣餒,但不能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