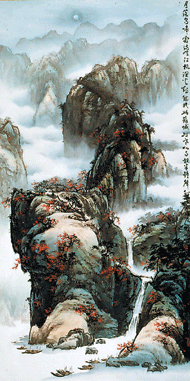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唐朝張繼很特別,原本沒甚麼詩名,卻只因這一首〈楓橋夜泊〉成為家喻戶曉的詩人。
曾有人質疑:寺廟夜半不可能有鐘聲,擾人清夢。提出這個問題的正是宋朝大文豪蘇東坡的老師歐陽修,結果惹來後代許多人為這首詩辯解:
宋人王直方在他所著的《詩話》中引用于鵠的詩:「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又白居易詩:「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皇甫冉詩:「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蔡正孫《詩林廣記》中亦引溫庭筠詩:「悠然旅思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這些都是唐代詩人所聽到的各地半夜鐘聲。范元實《詩眼》又從《南史》找到半夜鐘的典故。
《石林詩話》又證明南宋時蘇州佛寺還在夜半打鐘。又有人認為當時寒山寺的和尚確實有半夜敲鐘的習慣,稱為「無常鐘」。最後歐陽修被認為少見多怪。
然而這些紛紛擾擾似乎與詩的創作無關。不管寺廟夜半會不會敲鐘,這首詩所表現出來的意境夠令人感動,所以它便成了千古的絕唱,同時引起了歷代許多畫家的共鳴,「楓橋夜泊」也成為畫家喜歡入畫的題材。
我畫這幅畫,並不是楓橋當地的寫生,而是根據我所體會的詩意,創造出這樣的景象。
藝術所追求的是美的感動,若處處要追根究底,藝術就會變成一件無甚有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