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是詩人,也是詩學家,在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創作中,關涉到現代詩問題,多有精湛獨到見解。他將新詩創作視為一門藝術,且經由自身強烈的藝術自覺,使洛夫在各類題材,形成高標獨樹的美感風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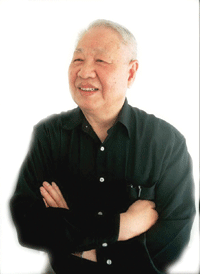 我在十六歲時即閱讀洛夫的詩集《無岸之河》,書上滿滿都是我的註解跟習作。當然,依那時的人生經歷,只能算是「誤讀」而已。1995年我為了在其作品研討會,與洛夫對談而做的筆記上,寫著:「不必解釋〈石室之死亡〉的晦澀與意義,如果把詩列為純粹藝術的一種,那麼有些作品將可省略過多的註解。比如現代派的畫、雕刻……而詩,有些原本不具『具象化』的條件,乃以『意』或者『念』為主導,每人的動念不同、程度有別,故賞詩猶如個人參禪。」
我在十六歲時即閱讀洛夫的詩集《無岸之河》,書上滿滿都是我的註解跟習作。當然,依那時的人生經歷,只能算是「誤讀」而已。1995年我為了在其作品研討會,與洛夫對談而做的筆記上,寫著:「不必解釋〈石室之死亡〉的晦澀與意義,如果把詩列為純粹藝術的一種,那麼有些作品將可省略過多的註解。比如現代派的畫、雕刻……而詩,有些原本不具『具象化』的條件,乃以『意』或者『念』為主導,每人的動念不同、程度有別,故賞詩猶如個人參禪。」
文學副刊 連載長詩的第一人
洛夫的詩一直讓人誤讀著,這代表他被貼上過多的標籤,給人多元思考、甚至迷亂的混沌狀態。加上洛夫是多方跨界創作的詩人,他的作品透出西方超現實的前衛,東方的超然禪味,是以中國傳統抒情為基礎,融合了東西方的哲思,不小心打開了後現代的文字形式之門;他的詩緊抓著現代感,有時令人透不過氣來,但那些預留空間的禪詩,則又放得很有意境。洛夫在詩中裝潢排設的功力,不論是熱鬧的西方裝置藝術,抑或簡潔而意味深遠的東方情調,都令人拍案稱絕!
洛夫於七十歲後旅居溫哥華,並將此地書房取名「雪樓」,自此潛沉創作、書法、思考創作與人生的必然關係。1999年完成三千多行長詩《漂木》,並首開文學副刊上連載長詩的第一人!這些年來洛夫受邀兩岸三地,活動頻繁,更顯其文學地位的尊崇。在生活的靜與動之間,詩魔的近期近況與體悟,可能是台灣讀者所急欲了解的。於是我們安排了以下的訪談:
年近八十足跡遍及兩岸三地
顏:我常在台灣的《文訊雜誌》跟中國各地的詩刊、海外華文刊物跟報紙上,看到您到處受邀演講跟參與研討會,請問這幾年來您參與了哪些比較深刻的藝文活動?

洛夫全家福。
洛:自2000年《魔歌》獲選為台灣文學經典三十之一前後,我的行程就遍及兩岸三地。較為重要的像是2004年獲北京「新詩界國際詩歌獎」、台灣「中國文藝協會」贈與「終身榮譽獎」、同年九月在溫哥華,我創立「漂木藝術家協會」出任會長,文友並舉辦一場洛夫詩作譜曲的大型音樂會,引發當地的注目;2005年名列台灣舉行的「十大現代詩人」票選榜首、獲大陸城市詩歌研究所頒贈的「新古典天王」獎座;2006年受聘加拿大《北美楓》詩雜誌榮譽社長、北京師大珠海分校「國際華文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五月由福建文聯在福州舉辦「洛夫詩歌朗誦會」、十月在上海舉辦「因為風的緣故-洛夫詩歌朗誦會」;我的詩與散文也陸續被選為各地華文的中學教科書裡。行程很多,但是年近八十的我,還是風塵僕僕帶著夫人一起旅遊。呵呵,這可能是長年寫書法的好處吧!(老師的頭髮雖花白,但氣色非常好、精神十足。)
今年的行程分兩段,四月初到達香港,之後經由深圳再轉長沙等地停留一星期,期間於湘南大學演講跟朗誦;之後到江南參加「洛夫與20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這是由香港大學、蘇州大學、武漢大學、徐州師範大學合辦的,共有十餘篇論文發表。然後回到溫哥華作準備,十月又到山西太原展出書法個展,也在那裡慶祝我跟瓊芳結婚四十六年紀念。大家對我很熱情,所展出的大小書法65幅,通通被買走,當地文友也提早幫我暖八十大壽。
當月下旬轉湖南鳳凰縣,由香港啟雄集團、深圳作協與當地省縣作協合辦「長詩《漂木》國際研討會」,台灣的白靈、簡政珍亦有提出研究論文,是一場規模很大的詩論發表會。
回顧與沉澱 詩歌全集將出版顏:真是老當益壯!聽說您五十歲才開始真正練習書法,至今您的書法變成許多人投資的藝術品,那我們得好好保存老師的真跡跟書法作品。只是因為您人在國外要聽您演講,機會就少了,至為可惜。另外,您在溫哥華的生活是怎樣安排呢?
洛:讀書、創作、寫書法、在附近散散步,還有吃喝玩樂……也在當地辦一些藝文聚會、讀書會,參加者有來自各地的華人跟加國朋友,我家彷彿是那邊的藝文沙龍,不時都很熱鬧的。其實我溫哥華家的院子裡,種了很多花草,我常常拈花惹草一番,心情很愉快。
顏:瓊芳師母的好手藝,想必征服了各地文友的胃!那老師有計畫再寫長詩嗎?
洛:從壯年的〈石室之死亡〉六百多行,中間還有《血的再版》長詩,隔了四十多年才寫出三千行的《漂木》,其他如近年的〈背向大海〉一百五十多行。長詩不好寫呀!這是很耗心力的寫作工程。
 「凡人二重唱」之一的音樂人莫凡(左)是洛夫兒子,計畫幫洛夫的詩譜成曲。
「凡人二重唱」之一的音樂人莫凡(左)是洛夫兒子,計畫幫洛夫的詩譜成曲。倒是一直在整理我的詩選集,已匯整為四大冊《洛夫詩歌全集》,將在2008年台灣的普音文化出版。我年紀大了,該是回顧跟沉澱的時候。我兒子莫凡(「凡人二重唱」之一的音樂人)近年也幫忙譜我的詩成曲,日後打算出版音樂專輯,但也是慢工出細活,才收了數首而已。這兩件事情是目前我較掛心的。
一生漂泊 空無反應人生顏:老師邁入八十歲,對人生跟創作有何特別的感悟?
洛:我這一生對漂泊的體悟,從少年到三十多歲(離開家鄉,參與各項戰役,出生入死)是「真假如夢」,中晚年欲尋覓精神的家園,以反制我對生命的不確定感,但終不可得。想這輩子走過那麼多地方,參與過文的、武的眾多事件,卻逐年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嚴重失落。也許透過不停地書寫這種「現實的失落」,才能在心靈上獲得一絲絲彌補;因為找不到心靈故鄉的盡頭,所以刺激自己不停的叩問、解答。
我在此要呼籲:傳統是回歸不了的,但至少我們必須「回眸」觀看、尋看身為中國子裔的生命本質、價值的高度。那些美好的文化並非嘴裡的文言文,而是可以落實在平常生活的態度、心靈追索的目的上。傳統是可以歷久彌新的,不要離它太遠呀!
而面對這一生的流離,我的心境恰好呼應了禪宗、老莊的「空無」。空無,正反映了我對人生到頭來的「空」,是悲劇觀的。我為什麼寫詩?別人不清楚,詩有一種「無用之用」的包容,人們透過文字去追問萬物萬事,詩對我而言,是一個生命悟道的蒲團!你看我詩集的書名,《石室之死亡》、《天使的涅槃》、《無岸之河》、《時間之傷》、《因為風的緣故》、《背向大海》……哪一個不是對人生本質的叩問!時間河流上打禪的詩與書法。
好作品具時代穿透力顏:老師,聽您這麼說,我心裡很受震撼,有佩服、也感心酸……您剛剛提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我想請教,書法是傳統的,而現代詩是新的體例,您後來將兩者融合並且宏發,對此您是否有特殊的意義?
洛:好的作品絕對具有穿透時代的力度。不管是傳統的詩詞、藝術,至今大家仍朗朗上口,誰說現代詩就不會成為日後的文化瑰寶?我成長的時代橫跨了多個世代,承接舊有藝文知識,也接受新潮的觀念,我覺得新舊兩相結合,能拉攏不同世代的人來進入藝文世界,這不是很好嗎。一個好的藝術家只求作品的高度,技法與體例只是他呈現的途徑,無關傳統與前衛。我藉著書法表現我的詩句,也是讓現代詩透過其他途徑,讓更多人看到。畢竟我先是一位詩人,再是半路出師的書法家。
顏:您近年在大陸展書法與受邀訪談次數較多,台灣有沒有考慮來個大型的詩書展?
洛:這些年我在台灣也有一些展覽,像新竹科學園區的展出、中華大學藝文中心的書法展,口碑也都很好呀。新竹那場也是作品賣光光呀,科技新貴若能投入藝文市場,多買藝術品,多買書閱讀,多從事藝術欣賞,台灣的創作者才能有舞台發光發熱呀。

洛夫(右起)、陳風子、瘂弦於漂木藝術家聯展合影。
由於洛夫老師隔天將進行白內障手術,故訪談進行約三小時,即讓老師休息。筆者感覺洛夫的思維與精神非常活潑,一點也不像八十歲的耆老。而他對藝文創作的精進,實則來自於對生命的漂泊感,這點讓我一時胸臆悲傷;聽到「空無」之說,更感受到大詩人對自己一生起落、名利貴賤的豁然。「詩魔」的魔不是心魔,而是讓讀者迷戀他的無窮魔力,他的詩與書法將一如所期許的,足以在時間河流上打禪,讓有緣者一起跟隨著他的意念,體悟生命的珍貴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