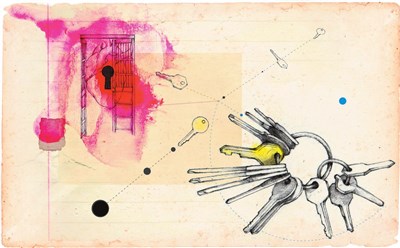 如花漸放的日子
圖/林役勵
如花漸放的日子
圖/林役勵
記得上大學以前,父母親姐姐和我,一家五口從未擁有過一串鑰匙。
那時台東的老家近海,瓦片屋前只有一道斑駁蒼蒼的木門徹日徹夜敞開,因為病弱緣故,不時能聽見它在海風中呻吟,到了夜晚,才勉強瞇眼睏去。
木門有鎖,但鎖的面容早被強壯海風欺凌得面目全非,僅悻存一個胖得連壁虎都能鑽入的鎖孔猶在頑強抵抗,如常發出慄人黑邃。事實上,木門根本老得不中用了,連鎖都上不了,但不知是否因鄉下人天性樸直,心腸不似開鎖關鎖那般繁複曲折,從小至大,也未曾聽過哪個竊賊見我家木門可欺,便狠狠偷偷地踹上幾腳。
只是我總不免好奇,那支木門鑰匙究竟何方物去了。因為鎖孔關係,我猜測那支鑰匙肯定有些重量,但委實可惜,始終沒能重到在家中任一人的腦海裡砸出半點記憶的波。它連一聲再見也不說,就這麼丟下木門,憑空消失尋不著。我猜想,它定是逃家了,抑或仗著母親終日在門前挑揀青菜,在後院洗晒衣服,需要不時呵護著家,便大膽得玩耍不歸。
相較已不知何處可尋的木門鑰匙,父親那支計程車鑰匙,便盡責得讓人想彎九十度的腰向它鞠躬表示敬意。雖然我沒摸過那支孤獨沒有朋友的鑰匙,但印象卻極為深刻。小時候,小小島嶼老讓我聯想得極為遼闊,總感到父親的計程車像方旅蓬,在盛夏的觀光時節,鑰匙一大早便帶著父親四處旅行,彷彿卡通片裡騎著駱駝橫跨忽濛濛沙漠要到各地交易的商隊。這般聯想,總也使我好想跟那支鑰匙作作朋友。但不管如何想像,都是對遙遠世界的十足嚮往,恨不得能夠添上一對翅膀奮力飛去。
記得有回,國小作文課寫「我的志願」,寫到長大後希望和父親一樣當個計程車司機,四處旅行。詳細內容如何,早已忘光,只是永遠忘不了父親看了作文後一聲不吭就給我一張悲憤的臉,然後賞了兩巴掌。那兩巴掌就這樣將志願打得一路翻轉前進,從作家到軍人到老師到醫生,總之,只要不做壞人不當計程車司機,父親覺得什麼志願都好。
對於父親,還有個深刻印象。
每當夏日清晨,我仍在夢的邊緣欲走還留而麻雀已在電線桿上比賽跳遠的時候,我便會聽見那支同父親一般具有削瘦身形的鑰匙,正和父親一起「喀喀」奮力敲醒沉睡中的計程車。而在寂默的夜晚,當父親悄悄駛車回來,將攢來的紙鈔捲成條狀交給母親後,那支顯得疲累的鑰匙,便會在冰箱的頭頂上給一個深情而幽微的吻,「噠」一聲,然後無聲酣眠而去。
也許是童年的記憶狀如大聲公,要負責隨時叫醒成年後仍和父親無法親近的我,直至今日,無論是清脆的「喀喀」或是細弱的「噠」,這兩個聲音在我的記憶裡都被放大成高分貝,一想起便響亮的盤桓不去,成為記憶中我少言父親的聲音。
離家上大學後,原本遲緩的生活也跟著上了自強號,愈行愈快。到了台北學校,第一件事,便是被迫在新土地上栽植一串鑰匙,從那時起,我與鑰匙共生共養的關係也宣告開始。
首先,是學校宿舍的房間鑰匙,一支屬於喇叭鎖的鑰匙。至今我仍不明白,喇叭鎖為何稱作喇叭鎖,從未聽它發出任何沖天高亢的聲音,分明靜靜的不起眼。倒是住進宿舍後,老聽見舍監對著麥克風宏亮廣播,內容千篇一律,都說近日宿舍竊賊猖獗,要學生多注意隨身財物。那種早到晚,不厭其煩的提醒,像是厲鬼橫行需要誦好幾部經來超度,弄得宿舍裡草木皆「賊」,莫名就要對人不信任起來。
其實整棟宿舍裡最好拐騙設計的,正是喇叭鎖。
有回不小心將自己關在房門外,深夜求助無門,便領教過隔房同學以一張電話卡輕鬆替我開門的絕技。電話卡像忍者走壁,沿著門縫欺到喇叭鎖身邊,一陣左拐右彎,門便開了。拔卡相助的同學說,這招專門用來對付喇叭鎖,不過功成後電話卡也沒好下場,多半遍體骨折,壯烈犧牲。此法雖是旁門左道,但因好奇仍是學了起來,說是備而不用,其實是貪圖不按常規行事的鬼祟快感。於是,開自己房門時,若四下無人,必是捨鑰匙,從皮夾拈出一枚捨不得丟棄的獨門暗器,想像自己是名刺客,冷酷的,朝喇叭鎖深處的心臟刺去。
大學時代,在使用排行榜上屈居宿舍房門鑰匙的,便是打工地方的鑰匙。
大一下那年,提款卡遺失後,父親便將郵局存簿的提款卡交給我。沒錢時,就去提吧,父親簡單的說。事後幾度要歸還,父親皆要我留著。於是父親那支長年奔波的計程車鑰匙,就以電腦密碼的方式祕密陪伴了我多年,並經常給我最實質的幫助。只是,私立大學的昂貴學費總讓我罪惡感叢生,當下選擇以打工方式告解,渴望多少能自給自足。
打工地點在學校餐廳冷飲部,年輕的老闆娘比學生還像學生,打工第一天便給了我兩支鑰匙,一支負責餐廳大門,記得當時大門鎖極為曲折,裡頭像藏了一條盤踞的大蛇,插入後得旋上好幾圈,才能推啟。另支鑰匙,則負責冷飲部前的長形門簾,門簾體態似扇,收攏起來就算開張。
我一星期打工四個晚上,從沖泡搖煮各式飲料,到洗刷圍裙器皿、拖地、點貨等等,全屬我的工作範圍,一趟下來,即使是陰冷冬天,也要汗流浹背到夜裡十點。當時,年輕的身軀還不畏勞動,縱算承載過多疲累,給上一覺好眠,也能輕易打發。(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