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愛其誰》背景在一九六○年代的西德,當時德國尚未統一,全歐瀰漫反動的風潮,熱愛文學的青年柏瓦和崇尚自由的女子古德倫相戀,未婚生子,兩人合組出版社,企圖藉文學在動盪時代產生影響力。但事與願違,出版工作困難重重,柏瓦四處留情又逃避現實,讓古德倫忍無可忍,遇見思想左傾的富家子安德烈斯,讓她不惜拋棄柏瓦和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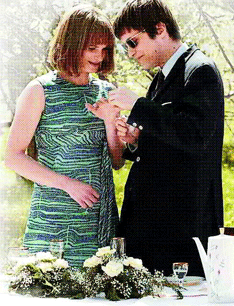 子,投身德國恐怖組織「赤軍旅」。
子,投身德國恐怖組織「赤軍旅」。
《捨愛其誰》導演安德烈斯.凡伊爾,中學時期即開始關注歷史,熱衷社會觀察,受名導演奇士勞斯基啟發,決心當電影導演,開始是拍紀錄片,二○○一年完成以「赤軍旅」恐怖分子沃夫岡葛拉姆斯為內容的紀錄片《黑盒子》,頗受注目,讓他接下來經近十年的構思籌備,編劇並導演與「赤軍旅」有關的第一部劇情片《捨愛其誰》。
捨我其誰 即知即行
本片根據真人實事改編,原英文片名《If Not Us,Who?》,出自聖經注釋家學者希勒爾(Hillel)的名言,完整文句為「If Not Us ,Who? If Not Now,When?」直譯為「若非我等,更待何人?若非此刻,更待何時?」簡潔有力的十六個字,原本象徵「捨我其誰,即知即行」的慷慨激昂,卻被許多人扭曲成某種偏激的情愫,企圖用作他們叛逆反動的依據。片中的柏瓦、古德倫、安德烈斯,都是迷思誤解那句話的犧牲品。
柏瓦是納粹詩人之子,原本不想生孩子的父母,因為奉行希特勒鼓勵德國人生育的「優生學」教條,才生下他。柏瓦遺傳父親顯性的文學才華及隱性的反動基因,當他面臨工作與情感的挫折,生活與經濟的壓力,反動的基因爆發,不只顛覆他的理智與才華,藉情欲、毒品等麻醉自己,自毀人生。
古德倫出身平民階級,是家中唯一能受教育的小孩,在期望中長大的她,自我期許甚高,本以為遇見柏瓦會讓她的人生更不平凡,結果事與願違,因而古德倫轉為依附激進分子安德烈斯,和他一起加入「赤軍旅」,到處製造暴動,看似為愛闖天涯,或是被視為伸張女權、打倒資本主義,其實她製造社會混亂的動機和行為,已凸顯自己的理性和理想全面崩潰。
安德烈斯出身靠資本主義致富的豪門,衣食無憂,讓他有時間可以上夜店,和男男女女談戀愛,還不過癮,聚眾搞暴動,名為開創「理想新世代」,但毫不考慮理想是否能普惠眾生?還是自我滿足?導致他和他「赤軍旅」在市區放炸彈等偏激行動,不僅害人害己,更將原本可能改革惡質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炸得面目全非。
納粹遺毒的歷史傷痕
二○○九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赤色風暴》,對「赤軍旅」的興滅成敗有更犀利的批判,《捨愛其誰》形同《赤色風暴》的前傳,聚焦「赤軍旅」剛成立的三個關鍵人物,將他們的愛情關係與社會脈動層層交疊,並剝揭納粹遺毒在二次戰後,仍威脅許多德國年輕人的思想,讓片中三位主角的命運,宛如捲進鉸鏈裡的三隻手,血肉模糊。
檢視歷史傷痕,是許多國家電影歷久不衰的題材,近年歐洲影壇與發動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相關的電影,就包括二○○八年贏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偽鈔風暴》,二○○九年讓凱特溫絲蕾贏得奧斯卡影后的《為愛朗讀》,同年贏得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的《白色緞帶》等片。
不過傷痕的造成始終來自於人,人難免傷人或受傷,但一傷再傷,就必須痛定思痛檢討改進。而無論傷痕電影或文學創作,透視人性,省思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絕不能片面思考或論定,否則可能產生以偏概全的盲點。
片名浪漫,其實內容議題深沉複雜的《捨愛其誰》,尤其女主角古德倫心碎時不怕碎玻璃刺痛,不代表她特別勇敢;一錯再錯,顯示她浪費了聰明和勇氣;反觀她入獄後,管理囚犯的女警對她說:「人往前邁進四步,必要時也要學著後退三步,重要是永不放棄。」古德倫為何至死執迷不悟?觀眾看完《捨愛其誰》應該會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