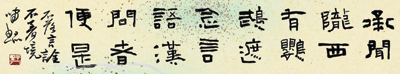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有一則對話。
《景德傳燈錄》有一則對話。
睦州道明禪師問:「你從哪裡來?」
僧人答:「瀏陽。」
睦州再問:「你師父對佛法有什麼體會?」
僧人答:「遍地行無路。」
睦州:「你師父真有說過這話?」
僧人:「說過。」
睦州禪師拿起柱杖便打:「你這只會學人說話的傢伙。」
「遍地行無路」是指「遍地行走,沒有一定的道路。」僧人的師父確是對佛法頗有體會,無論什麼路,都通向佛的境界,都指向開悟的境界,所以遍地無路都是路,遍地無門都是門。
但這是僧人的師父自己的體會,不是僧人的,僧人只如鸚鵡般學舌照搬師父的「言語」,被言語言詮所縛,這是開悟的大忌,所以遭禪師杖打。
《五燈會元》也有一則對話。
有僧人問虎溪庵主:「和尚哪裡人?」
虎溪答:「隴西人。」
僧人又問:「聽說隴西有鸚鵡,是真的嗎?」
虎溪答:「是真的。」
僧人說:「和尚莫非也是鸚鵡?」
虎溪禪師便學鸚鵡叫聲。
僧人大笑:「好一隻鸚鵡!」
虎溪禪師拿起棒子便打。
這位僧人心懷不軌,想測試虎溪禪師的修行工夫,設下「言語」的圈套,所以見虎溪禪師有問必答,抓住機會便嘲笑虎溪是一隻鸚鵡,想對虎溪示機,看他如何應對,虎溪禪師順勢而為,學起鸚鵡的叫聲,不料,僧人反而中計,說「好一隻鸚鵡」,說出「鸚鵡」兩字,掉入了「言語」、「言詮」的陷阱,聰明反被聰明誤,虎溪執棒便打。
第一則公案,僧人學師父「遍地行無路」的話,只是複誦師父的言語,沒有自己的體會,禪宗稱之為「念言語漢」,學人說話,當然是不折不扣的鸚鵡。
第二則公案,僧人設計,想讓虎溪禪師成為一隻「學舌的鸚鵡」,但虎溪智慧頂尖,他只是學鸚鵡的叫聲,學鸚鵡舌頭的俐落,是「舌上學鸚」,而不是「學人說話的鸚鵡。」僧人因為禪師的「鸚鵡演出逼真」,反而中計,說出「好一隻鸚鵡」的嘲語時,著境著相,復又跌入語言詮釋的陷阱,自己成了真正的鸚鵡。
禪宗主張「不落言詮,不著境。」第一位僧人學人說話,落入言詮,該打;第二位僧人,聽到禪師逼真的鸚鵡聲,說禪師「正是一隻鸚鵡」時,被外境所惑(著境),又落入言語的牢籠中(落言詮),所以更該打。